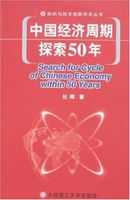如果前辈们没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很可能会丧失其全部权威性。谢冕把这一股年轻人的诗潮称为“新的崛起”,是富于历史感,表现出战略眼光的。不过把这种崛起理解为预言几个毛头小伙子和黄毛丫头会成为诗坛的旗帜,那也是太拘泥字句了。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的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他们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牧歌传统和60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梁小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他们在探索那些在传统的美学观看来是危险的禁区和陌生的处女地,而不管通向那里的道路是否覆盖着荆棘和荒草。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诗风有一种探险的特色,也许可以说他们在创造一种探索沉思的传统。徐敬亚说:“诗人应该有哲学家的思考和探险家的胆量”,这倒是我国当前的一种现实,迷信走向了反面,培养了那么多的哲学头脑,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他们的这种思考和传统的美学观念不同之处乃是徐敬亚所说的诗人甚至“应该有早于政治家脚步的探讨精神”。从习惯于文艺从属于政治家的文坛看来,这不免有点“异端”了。当革新者最好的诗与传统的艺术从属于政治的观念一致的时候,他们自然成了受到钟爱的候鸟。正因为这样,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得到异口同声的赞许。但是,他们有时也用时代赋予他们的哲学的思考力去考虑一些为传统美学原则所否决了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的幸福,在我们集体中应该占什么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如何才能达到,分歧和激烈的争辩就产生了。它集中表现为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在年轻的探索者笔下,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政治标准。社会政治思想只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可以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决定某些意识和感情,但是它不能代替,二者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规律。例如政治追求一元化,强调统一意志和行动,因而少数服从多数,而艺术所探求的人的感情可以是多元化的,不必少数服从多数。政治的实用价值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的非实用性,是有矛盾的,正如一棵木棉树在植物学家和在诗人眼中价值是不相同的一样。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原则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那么革新者比较强调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在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价值也不能离开个人的精神的价值,对于许多人的心灵是重要的,对于社会政治就有相当的重要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宗教),而不能单纯以是否切合一时的政治要求为准。个人与社会的分裂的历史应该结束。所以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我们的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恢复了理性,这种恢复在最初的阶段是自发的,是以个体的人的觉醒为前提的。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地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而这种复归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在艺术上反映这种进步,自然有其社会价值,不过这种社会价值与传统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不同罢了。当舒婷说:“人啊,理解我吧。”她的哲学不是斗争的哲学,她的美学境界是追求和谐。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从理论的表述来说,这可能是有缺点的,离开了矛盾的同一,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但在创作实践上,作为对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的一种反抗,它正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折光。从美学来说,人的心灵的美并不像传统美学原则所限定的那样只有在斗争中(在风口浪尖)才能表现,谁说斗争能离开统一,矛盾不能达到和谐呢?因为据说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就应该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瞪着敌视的目光,怀着戒备的心理,戴着虚虚实实的面具,乃至随时准备着冲入别人的房子去抄家、去戴人家的高帽吗?在舒婷的作品中常有一种孤寂的情绪,就是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反常畸形的一种厌倦,而追求真正的和谐又往往不能如愿,这时她发出深情的叹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一种典型化的感情?为什么只有在炸弹与旗帜的境界中呐喊才是美的呢?不敢打破传统艺术的局限性,艺术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一种新的美学境界在发现,没有这种发现,总是像小农经济进行简单再生产那样用传统的艺术手段创作,我们的艺术就只能是永远不断地作钟摆式单调的重复。梁小斌说:“‘愤怒出诗人’成为被歪曲的时髦,于是有很多战士的形象出现。一首诗如果是显得沉郁一些,就斥为不健康。愤怒感情的滥用,使诗无法跟人民亲近起来。”他又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给普通的玻璃器皿以绚烂的光彩;从内心平静的波浪中,觅求层次复杂的蔚蓝色精神世界。”这些话说得也许免不了偏颇,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他们一方面看到传统的美学境界的一些缺陷;一方面在寻找新的美学天地。在这个新的天地里衡量重大意义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中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的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与艺术传统发生矛盾,实际上就是与艺术的习惯发生矛盾。在生活中,要提高人的地位,自然也有习惯的阻力,但是艺术的习惯势力比之生活中的习惯势力要顽强得多。因为在生活中,人们是以自觉的意识指导着人的思想和实践的,以新的自觉意识去克服旧的自觉意识,虽然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总是属于理性范畴,总是比较单纯。而在艺术中则不完全是理性主宰一切,它包含着感情。泰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在一股赋有诗人气质的人身上,都是不由自主的印象占着优势”,“若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得肯定其中有个自发的强烈的感觉”。艺术的感情色彩使它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自发的”一面,这一面有时还“占着优势”。长期的大量的艺术实践不但训练了艺术家的意识,而且训练了他的下意识或者潜意识。这样,使他的神经在感情达到饱和点的时候,依着一种“不由自主的”“自发的”习惯,达到一种条件反射的程度。习惯,就是意识与下意识的统一。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养成自己独创的艺术习惯都是艰难的。意识和潜意识都是建立在长期经验基础上的。个人、民族、时代的美学独创性,都渗透在这种习惯之中。年轻的革新者要克服一种习惯的拘束,同时,要确立一种新的习惯。不论克服还是确立,光凭自觉意识是不够的。光凭自觉意识就是光凭概念,它同时要和那“不由自主的”“自发的”潜意识打很久的交道。自觉意识不能完全战胜下意识,正如法国的语音学家可能读不好英语的重音一样,又如吴语区的语音学家可能说不好普通话中的卷舌的辅音一样。因为习惯是一种条件反射,形成了一种潜意识,是自觉意识不能管束的,它的存在就是反应固定化的结果,是很难变化的。恩格斯所说的传统的惰性在这里可以找到一部分注解。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顾城在《学诗札记》中说:“诗的大敌是习惯——习惯于一种机械的接受方式,习惯于一种‘合法’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一种公认的表现方式。习惯是感觉的厚茧,使冷和热都趋于麻木;习惯是感情的面具,使欢乐和痛苦都无从表达;习惯是语言的套袖,使那几个单调而圆滑的词汇循环不已;习惯是精神的狱墙,隔绝了横贯世界的信风,隔绝了爱、理解、信任,隔绝了心海的潮汐。习惯就是停滞,就是沼泽,就是衰老,习惯的终点就是死亡……当诗人用崭新的诗篇,崭新的审美意识粉碎了习惯之后,他和读者将获得再生——重新感知自己和世界。”也许把重新感知自我和世界当成革新者的任务并且痛快淋漓地宣告要与艺术的习惯势力作斗争,这还是第一次,因而它启发我们的思考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的表述,我们还是要禁不住吹毛求疵一下,这里多少有些片面性,透露出革新者美学思想上的弱点。因为习惯,即使过时的习惯,也不光是停滞的沼泽,它还包含着过去的成就和经验。当革新者向习惯扔出决斗的白手套时,应该像梁小斌那样:“我必须承认‘四人帮’的那些理论也在哺育我,它也变成阳光,晒黑了我的皮肤。”自然,我们可以说“四人帮”的理论不是我们的传统的习惯,但也不可否认它是我们传统和习惯的畸形化,人总是要在前人积累的思想材料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前进的,前人提供的不可能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但人类正是在这并不绝对完美的阶梯上攀登的。光凭一个人的才华,光凭自己的生活积累是成不了艺术革新家的。《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王冕,孤独地反复地面了好多年荷花,没有任何学习与参考的资料便卓尔成家,有了惊人的创造,从艺术理论上讲,这是不科学的。王冕的方法是从零开始的原始人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艺术水平来的。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总是既要从生活出发,又不能完全排除从艺术出发的。西洋画从写生开始,中国画从临摹开始,都是反映了规律的一个侧面,二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马克思说:人是接着美的法则创造的。就是说人在客观现成材料(素材)面前不是像动物那样被动的。美的法则,是主观的,虽然它可以是客观的某种反映,但又是心灵创造的规律的体现。在创作过程的某一阶段上,美的法则是向导,是先于形象的诞生的。它又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活在传统的作品和审美习惯之中的。要突破传统必须有某种马克思讲的“美的法则”,必然要从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内核”。习惯只能用习惯来克服,新的习惯必须向旧的习惯借用酵母。不是借用本民族的酵母的一部分,就是借用其他民族的酵母的一部分。只有把借用习惯的酵母和突破习惯的僵化结合起来才能确立起新的习惯,才能创造出更高的艺术水平,否则只能导致艺术水平的降低。目前年轻的革新者们自然面临着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但是如果他们漠视了传统和习惯的积极因素,他们有一天会受到辩证法的惩罚。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们似乎并没有忽略继承,只是更侧重于继承他民族的习惯。但是这种习惯与我国本民族的习惯的矛盾有时是很深的。虽然新诗史上大部分有独创性的流派,都和外民族独异的艺术刺激分不开,但是,即使其中的大诗人也还没有解决两个民族艺术习惯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走向反面,产生闭关自守或者全盘民族化的倾向。新诗的革新者如果漠视这样的历史经验,他们的成就将是比较有限的。不过,我们并不悲观,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并不像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全部蓝图。他们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自己还幼稚,舒婷在《献给我的同代人》中说: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
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探索既是坚定的,不怕牺牲的,又是谦虚的,承认自己的脚步是孩子气的。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他们肯定会有错误,有失败,有歧途的彷徨,但是,只要他们不动摇,又不固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是可以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得到上帝的原谅的,同时,又会给后来者和他们自己留下历史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是不是会浪费,就要看我们善于不善于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为他们所接受了。
1980年10月21日—1981年1月21日
原载《诗刊》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