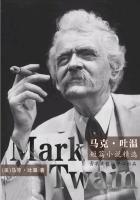张云利用几天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当年父母被冤枉的说明材料,同时还特别提到了他和弟弟在派出所后窗看到的父母被许大雷及协勤人员殴打的那一幕。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回想起来,好像就发生在不久以前,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还历历在目。父母被许大雷毒打的那一幕已经永远永远地定格在他的心里,让他经常想起,让他无法忘记。让他不能忘记的还有母亲和妹妹的死。
就在张云写好材料的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相当的篇幅报道了发生在南方某城市的连环爆炸案。仅仅相隔一天,上级就下发了通缉令,通缉此次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金如超,一个四十岁左右,秃顶,身体偏瘦,说话有些吐字不清的男人,同时配发了照片。
由于案情重大,影响极坏,各省、市、县、区公安局的上下级之间都立下了军令状。而许大雷和张云这些最基层的民警们则每天不分昼夜地出去堵卡、设哨,以最原始的方法检查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和马虎。他们不但要检查过往行人的身份证件,还要看看证件上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争取不漏查一人。
根据内部人士的分析,金如超有可能北上,至于北上到哪个城市,内部人士没有确切地分析出来。这就让所有的民警都处在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
那些天,无论是许大雷还是张云都累得筋疲力尽。每天十二三个小时守在毫无遮挡的交通路口。白天遭受太阳的曝晒,傍晚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好不容易轮到换班,又要抓紧时间去各村深入群众,看看有无生人来往,听听有无可疑线索。
说不清从哪一天起,张云的右小腿开始肿胀起来,开始只是局部肿胀,肿胀部位是从被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至整个小腿。因为派出所警力有限,开始时,张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为只是被蚊子叮了,毒血留在里面,挺一挺就过去了。谁知那天他在头昏脑胀之下一撸裤腿,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只见那条小腿已经完全变了颜色,仿佛腿上的皮肉都已经腐烂变质,花花绿绿的找不出一块正常的地方。用手一摸,热得发烫。张云放下裤腿,往许大雷这边看了看,见许大雷正在对一辆出租车进行例行检查。张云走过去,想向许大雷请假,到医院看一看他的腿。可刚喊了一声所长,张云就后悔了,于是赶紧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听见张云在叫自己,许大雷忙转过脸来,看见张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说:“张云,你要是觉得太累,就先在车斗里歇一会。”
下午,张云烧得越发厉害,为了不影响工作,不影响许大雷的情绪,他一直努力地坚持着。
晚上九点多钟换岗时,张云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他谢绝了许大雷提出的一块吃晚饭的建议,要独自一个人回派出所。半路上,张云拐向了镇医院,他要让医生看看他的腿到底怎么了。诊断结果是荨麻疹,医生给开了两样药膏外加一小袋棉签。借着医院走廊里昏暗的灯光,张云把药膏涂抹在腿上,然后骑上摩托车艰难地回到所里。
因为发烧,因为腿疼,张云连饭也没有吃就上床就寝。可他却无论如何也睡不踏实,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还是站在堵卡的路口,前后来往的车辆都向他隆隆地开过来,他在车辆中左躲右闪,大喊大叫,但车上的那些个面无表情的司机们却好像都看不见他,驾着车直向他冲过来,车身碾过他的身体,碾过他的腿……
半夜时,许大雷才姗姗而归。今天除了在楼下值班的两个民警以外,在所里睡觉的只有许大雷和张云两个人。许大雷轻手轻脚地走进屋来,拉亮了壁灯,灯的瓦数很小,灯光很暗,许大雷在这昏暗的灯光里走到自己的床前,坐下来,两手自然下垂,好半天没动一下。但思绪却没有停止,他还在回味着刚才的事情。刚才,在饭店门口,他很意外地遇到了镇长的老婆,他的老情人——马凤珍。关系已经非同一般的他俩很自然地一前一后来到僻静处,急不可待地一通缠绵。正当两人心旌摇荡打算向更深一层发展之时,远处传来了脚步声,于是他们赶紧分开,各奔东西。意犹未尽的许大雷在回来的路上一直都在想着这件意犹未尽的事,而且到了所里也没缓过神儿来。
虽然马凤珍不够漂亮,虽然许大雷还没有达到爱她的程度,但她毕竟是女人,有着女性的一切生理特征,而且是她主动投怀送抱的,这让正处在生理饥渴阶段的许大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坐怀不乱。
许大雷的目光又向桌子上移去,他又看到了高山的画像,此时画像上的高山正微笑着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他是我父亲,精神上的父亲。”许大雷想起张云曾说过的这句话,即而又想起了张云疯癫的父亲,心里一时慌慌乱乱的。
那一夜,许大雷和张云睡得都不好。
第二天早晨,趁着许大雷出去买早饭的工夫,张云把药膏再次涂抹到腿上。腿还和昨天一样,又黑又紫,肿胀难忍。看来,药膏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许多抹几次就能见效了,张云这样安慰着自己,同时找来体温计含在嘴里,测量结果:39。2度,这是张云可以承受的温度,他发烧的最高记录是39。9度。
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张云实在坚持不住了,于是就向许大雷请假,说腿疼,想去路边坐一会儿。许大雷一听,就有些着急,走过来问张云的腿怎么了,张云扶住那条病腿,还没等说话,许大雷就已经在他面前蹲下身,轻轻的一层一层地卷起他的裤腿……烧得迷迷糊糊的张云低头看着许大雷的后背和头顶,感觉他好像是自己小时候的父亲。
许大雷把张云送到镇医院,诊断结果是细菌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容易并发败血症。虽然这个结果和昨天的诊断大不一样,虽然许大雷和张云都不敢肯定这就是最权威的诊断,但医生建议的消炎退烧还是不会错的。这也是乡镇医院治病的一个万能药方。
张云扎上滴流以后,发烧的症状开始减轻。这倒不是退烧药这么快就起了作用,而是许大雷隔几分钟就往他身上搽一次白酒,这才把烧退了下来。
“要不,你先回去?”看着一直围着自己忙前忙后的许大雷,张云试探地说。“不用,等你扎完这瓶滴流咱俩一块儿回去。”许大雷的语气虽轻,却不容张云争辩。两个人沉默了一会,表情上都有一些不自在,于是就寻找彼此共同的话题,结果话题自然又扯到了工作上,扯到了正被通缉着的要犯,以及已经撒下的天罗地网。许大雷说:“我就不明白,这个金如超怎么就这么没有理智呢,他不知道杀人犯法,我看他是活腻了,不知道怎么作好了。”张云并没有马上接许大雷的话茬,而是思索了一会儿才说:“其实也无所谓理智不理智,他既然那么周密地准备和实施了这次爆炸,说明他的大脑没有问题,更不是一时的冲动,从这一点来看,我倒觉得他相当理智,他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能意识到实施爆炸的后果及自己未来的处境,但他还是无所顾忌地去做,这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出现了问题。我收集了许多罪犯犯罪前的资料,了解了他们的一些经历和遭遇。其中有一些人在犯罪之前都曾被深深地伤害过,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家庭、他人和社会的伤害和刺激,这些伤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但出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他们又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忍了下来,压抑在心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忍气吞声。其实这些经常忍气吞声的人才是最危险的,一旦外界对他们的伤害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报复心理,他们会不动声色地准备好一切。从开始有报复的想法到真正实施犯罪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这时他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那么他的报复心理就会逐渐淡漠,而如果他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或者遭受一些让他无法忍受的待遇,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了未来,没有了希望,那么他就有可能开始实施他的犯罪,有可能对曾经伤害他的人下手,或是报复整个社会。所以说,每个罪犯的犯罪动机都有很深的根源,而我们在卷宗上看到的仅仅是他们犯罪时的记录。作为公安人员,我们在制止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是否给当事人和当事人的家属造成过不应有的伤害;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公正执法;在处理纠纷时,面对上司的压力,朋友的请求,我们又有几个拒绝过,我们又有谁真正做到了对每一位当事人都一视同仁……”张云的脸有些铁青,牙也不由自主地咬在了一起。他想起了他的父母,想起了父母当年被许大雷殴打时的惨相。
许大雷感觉到了张云情绪上的变化,他尴尬地坐在那儿,不知道该对张云说些什么。过了好一阵,张云的情绪才缓和下来。他说:“所长我刚才有些激动,你不要介意,我只是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沉默了。
许大雷听出了张云对他的旁敲侧击。只有心里有愧的人才能一下子就听出张云所指的是什么,他甚至从张云的目光里看到了压抑着的仇恨,已经十二年了,张云对自己的仇恨依然存在。
张云虽然在最基层的派出所工作,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学习和努力,从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他一直想致力于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为此,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不少罪犯的家属和一些刑满释放人员。还利用他的职务之便通过关系找一些正在服刑的重罪犯人或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罪犯面对面地平等地沟通。
张云一直想探寻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的根源。他的这种想法也是源于他自己的经历。他清楚地知道,自从父母被错误地拘留以后,他就曾有过报复的想法,特别是母亲死后的那段时间,他的这种报复的心理越发强烈,几乎到了磨刀霍霍的程度。他把家里的那把中间带凹肚的杀猪刀磨得飞快,藏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他是那么频繁地想到了要报仇,是那么强烈地想到了要杀了许大雷。一天夜里,他趁着夜色的掩护来到了许大雷住的村子,凭着以前打听到的信息摸到了许大雷的家。他伏在窗台下的花丛里,听着屋里人的说话声和咳嗽声,想象着杀猪刀刺进人体时的样子。
那是多么紧张的一个夜晚,那是多么危险的一次埋伏。
那次张云在许大雷家的院子里一直趴伏了四个多小时,有好几次他都想跳进屋去手刃仇人,又有多少次他努力地深呼吸以让自己狂跳的心平静下来。张云伏在那里,理智与冲动、复仇与忍耐在心里频繁交替。最后他终究没有动手,他听到了屋里有女孩的声音,那声音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他仰起头,努力地抑制着满眼的泪水,他看见了满天的星斗,那满天的星斗正泛着清冷而肃穆的幽光,照着他的脸和他手上那把带凹肚的长刀。
星光之下,张云多么希望自己正经历着的只是一场梦境,连同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境。那么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会惊喜地发现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他的爸爸都还好好地、健康地活着。他们一家人还和以前一样,尽管辛苦却还团圆。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美好的想象而已,他的妈妈、他的妹妹永远不会回来。他的家也永远不会回到从前。
张云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这次复仇计划,哪怕是想法。他想把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他就是这么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想事情,做事情,而又不张扬。后来,张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这次经历,那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他完全放弃了复仇的念头是在他读高中以后,那时高山月月给他寄钱写信,像亲生父亲一样关心他、开导他。正是这个高山的出现让张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后来长大了,张云才知道十五六岁正是心理波动最大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从幼稚向成熟过渡的年龄,人在这个时候学好不难,学坏却更容易。如果在那个满天星斗的夜晚他没有把握住自己,那么他的一生也许就真的毁了。每每想起,他都忍不住后怕。这件事也让他明白了,对于年轻人来讲,犯罪与否有时仅仅是一念之差。
临从医院出来时,许大雷再次去找了大夫,问他除了挂滴流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让张云的腿快些消肿。大夫托着下巴想了一会儿才慢条斯理地说:法子倒是有一个,这是民间的一个偏方,我不敢说百分之百见效,但绝对没有副作用。大夫说的这个偏方就是将仙人掌的叶片捣碎,然后敷在患处。
派出所就有仙人掌,照着大夫告诉的方法,许大雷先把仙人掌洗净、控干,然后用小刀挖上面的毛刺。那些毛刺又尖又细,而且都长在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小窝窝里,每个小窝不过黄豆粒大小,一刀挖下去,刺没挖净,倒把掌肉带下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