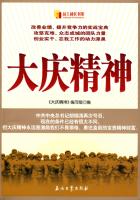我的问题是:所有戴望舒的诗都可以归入抒情诗之列,为什么一般文学史家还有诗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他归入象征主义者之列呢?
不但大学生无法回答,而且他们的教授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戴望舒的作品为什么不是浪漫主义的呢?
我举他的成名作《雨巷》为例,连戴望舒的第一个发现者叶圣陶都只说到他的这首诗开始了新诗节奏的新纪元。这话经常被文学史家所引用,当作权威的评定。其实叶圣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戴望舒是不主张诗的音乐性的,他在《论诗零札》中明白宣称,“诗应该去掉音乐的成分”。
其实关键在于象征主义诗人认为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直接把感情倾泻出来是很容易概念化、抽象化的,于是他们诉诸感觉,用感觉的变幻来代替感情的直接抒发。浪漫主义者的感情是强烈的激情,而象征主义者则是一种宁静的体验,不过他们不把自己的感觉作主观的表达,而是为这种主观感觉还有感觉以下的宁静的情绪寻找一种“客观的对应物”。
戴望舒在《雨巷》中所显示的就是把主观的情绪变成客观对应物的技巧。
他独自行走在狭窄的雨巷,希望遇到一个拿着雨伞的、像“丁香结着哀愁”的、有着“太息一样的目光”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动作是徐缓的、无声的,哀愁是淡淡的、朦胧的,而这一切正是戴望舒自己的特点。
我告诉他们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词句是姑娘拿着油纸伞独行在雨巷,“就像我/像我一样”无声地缓缓地走在孤独的哀怨之中,这正是主客观对应的连结点。
这个女性的形象,正是戴望舒自己内在的无声的哀愁的外在对应物。主观与客观性别不同,但是情感、感觉的特点则是统一的。
这种内在情绪的外在感觉化,特别表现在他后来在日本人监牢中所写的《我用我残损的手掌》中。本来,人面对世界抒发感情,可以运用眼、耳、鼻、舌、身等至少五种感觉,但是戴望舒却别出心裁,把他对于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和大后方仍然在抗战的整个感觉不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全部感觉来传达,而是把它集中在一种感觉(触觉)中的一个部分——手的感觉来表现。所以他强调了对于灰烬、对于血染的泥土的触觉感受,他摸到了河水的凉意和长白山透骨的冰寒,特别是黄河泥沙之滑,江南秧苗的柔,用这样的感觉来表现他对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人民的感受是很有象征主义的特点的。
象征主义回避直接抒情,而以感受状之。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的特点,他的诗才是象征主义的。
有一位很有修养的教授,叫许芥煜,他翻译了一本《20世纪中国新诗》,比北京出的《中国文学》英文版上翻译的要强得多。但是他也没有弄清戴望舒诗歌的象征主义性质,反而说戴望舒晚年写的大体都是“抒情诗”,这就把问题弄混了。这说明,要真正讲通戴望舒的艺术是多么的困难,这里需要有对诗歌艺术本身的理解。
任何一种理论只是在有利于理解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结构的意义上才有价值。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缺陷是达不到艺术形象、结构的深层奥秘,因而新一代的理论家,对之失望了;他们大都转向别的理论,但是别的理论,包括很风行的文化学理论,所遇到的仍然是无法回答艺术本身的问题。看来,只有回到艺术形象本身的分析中去才有希望。
8.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
美国大学生和教授,有时对于中国的现代新诗表现出不太理解的样子,特别是20年代的浪漫主义诗歌。这是因为在本世纪初,浪漫主义诗歌在美国诗坛已经不时髦了,那种把感情强化、极化的抒情方式,经过西方100多年的发展,已经使他们厌倦了。本来sentimentalism在20世纪初,被我们早期的作家翻译成“感伤主义”,也就是多愁善感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在当代英美语言中已带一点贬义;现在有人把它译成“滥情主义”,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在五四时期和20年代,中国人的多愁善感对于扼杀人情的礼教还是有一点革命的启蒙主义功能的。
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对外国人,特别是被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弄得对真正恋爱有点茫然的美国大学生说清楚徐志摩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我举“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为例,向美国大学生解释说,徐志摩这样的诗句是有一点反抗性和创造性的。他讲出了许多人,甚至文学革命大师都能讲的话,但是可贵的是他以他的生命为这句诗作了注解。
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是当时小说、诗歌、戏剧的共同主题,但是许多主张自由恋爱的文学前驱恋爱却不能充分自由。胡适是喊得最凶的一个,但他的婚姻是包办的。结婚以后,他的妻子并不能使他满意,他真正的意中人是另一个。后来,胡适和她在杭州有一次会晤,被妻子发觉,以大闹一场而终,从此胡适不敢造次。郭沫若也是一样,他最早的婚姻是包办的,他去日本后,陷入了一次恋爱,并且生下了儿女。可是道德的苦闷常常使他想着自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他才高呼反抗,以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欢呼毁灭旧世界和旧自我,让新世界和新自我像火中复活的凤凰一样享受温馨的欢乐,但他居然一直没有和那包办的妻子离婚。最奇怪的是鲁迅,他对旧礼教的批判是最彻底的了,但是他也有一个由他母亲包办的妻子。还是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突然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星夜赶回绍兴,不料是张灯结彩,在等待他作新郎。他并不喜欢那新娘,但为了不违抗母命,他只好委屈自己做了一个孝子,但几天以后他就走了,从此就把这个新娘还给了他母亲。在他和许广平有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以后,他本是可以和他的挂名妻子离婚的,但这位名叫朱安的女士趁鲁迅的兄弟作人、建人都在场的时候,双膝下跪,要求不离婚,永远让她服侍周氏老太太,至于鲁迅与谁再去结婚,她决不干预。鲁迅除了同意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鲁迅后来去了南方,待到四一二政变以后,他本是可以回到北京的,但这位朱安女士的存在,很可能是他和许广平定居上海,而把母亲和朱安放在北京的一个原因。
讲了这么多,我才转到徐志摩身上来。
当他发现自己另有所爱时,便非常果断地提出了和他的“发妻”张幼仪离婚,而不管无穷无尽的社会批评。那时连他的恩师梁启超都曾写了一封长信谴责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但是他顶住了,他把张幼仪的信给公布出来,可真有点大无畏的精神。很可惜后来他追求陆小曼,此人乃一交际花,在结婚后仍耽于社交,并且吸毒,还与一个医生有染。这使徐志摩十分痛苦,遂离开上海的家庭,应聘于北大,往来于空中交通,不幸于1931年死于空难。
徐志摩的诗绝大多数是他灵魂冒险的记录,他的诗相当成功,但是他的自由恋爱却是失败的。
对此,美国大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十分有同感。
后来我提起,在中国作家中,包办婚姻也有十分幸福美满的。例如茅盾与孔德祉白头到老;叶圣陶对他包办的妻子十分满意;而闻一多的包办妻子连字也不大认得,他还从美国写了长诗去给她,让她用手去摸字,说是便可感到他们心跳的一致,可惜这诗被他父亲截留了。当我说到“截留”(intercepted)时,美国女大学生惊叫起来。我说,这种美满有时像你们美国的买彩票,一下子中了三个头奖,于是课堂里所有女学生一下子都欢呼起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办婚姻之弊早已为人类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恋爱走向极端,又有可能导致光有自由而没有恋爱了。因而60年代以后,西方青年乃有试婚之举,但试婚的消极性似乎更大。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然在摸索。
9.丁玲为什么对沈从文那么刻薄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对于丁玲总是怀着某种别扭的印象,虽然这主要不是由于我对她的作品有什么偏见。说实在的,对于她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我是很喜欢的。我甚至认为,这本日记体小说给了茅盾在抗战期间用同样是女主人公的口气写的日记体小说《腐蚀》以重要的影响,那个女主人公在心理气质上就是有点莎菲女士的特点。这一点似乎被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忽略了。
我对丁玲怀有别扭之感,主要是因为我对丁玲为人的印象,我的主要根据,是她对沈从文的歧视。
本来在30年代,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曾经志同道合献身于文艺,而且共同组织过“红黑社”,出版《红黑》。尤其是在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曾经奔走营救,为文抗议,还陪同丁玲去探监。后来丁玲又秘密被捕,沈从文两次为文抗议,在丁玲出狱以后,沈从文还去看望过她。在沈从文当时写的记述丁玲和胡也频的文章中,他对于丁玲和胡也频献身于革命的行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虽然沈从文自己并不想投身革命运动。但是,丁玲在50年代初期成为文艺界领导,在党内和文艺界都有相当的发言权之时,眼见沈从文从北大教授的位置上被拉下来,备受歧视,苦闷得一度自杀,而且从此结束了创作生涯,她却袖手旁观,这实在是毫无道理的。沈从文即使按当时的标准,也绝对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然而,丁玲作为沈从文当年的好友,曾经在患难中得到人家关照的,却完全忘掉了往日的情分,既没有以正常的朋友的身份去拜访沈从文,也没有为沈从文的不公平遭遇讲公道话;相反,她在1952年为开明书店出版的《胡也频选集》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很不客气地说到沈从文——“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这种话说得极其刻薄,完全不像曾经是密友的身份。
丁玲这样对沈从文完全是不通情理的,这时沈从文已失去北大的教席,且又自杀未遂,成为北京文史馆的小职员,甚至是讲解员。丁玲不可能不知道沈从文的尴尬处境,但是她却理直气壮公然地表示了她对沈从文的藐视。
这不仅是丁玲个人的缺乏人情,而且是一种历史的风尚,当时,对于朋友、亲人稍有不合政治时尚者,则“划清界限”,避之犹恐不及。这在台湾和大陆是异曲同工的。丁玲当时正红得发紫,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又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处处觉得自己高人一头。沈从文当时已为文坛放逐,所以,在为文时稍稍损他一笔,实在是其庸俗的政治优越感的表现。在这里就隐藏着丁玲为人的自私。
由于是用最神圣、最光辉、最容易被时人接受的词句讲述出来的,因而就连这种显而易见的庸俗的优越感都被读者忽略了。
正是这种庸俗感使我对丁玲在50年代的许多文章产生一种反感,甚至在她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受非人的痛苦后,我仍然对她难以原谅。因为她直到80年代后期,在回忆文章中仍然对沈从文发了许多苛刻的议论,且不说那些议论完全站不住脚(这一点已经由《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作了澄清),就是在她得意时,对许多朋友(包括胡风)的伤害都毫无忏悔之词,从中也可见丁玲的人格与巴金相去甚远了。
10.陈寅恪的学术悲剧
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读书界颇为走俏,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有一点奔走相告的味道。早在50年代后期,我还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就听周扬在报告中说过: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不能像对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要求他进行思想改造,中央请他到北京来工作,他提出的条件是:不学马列。当时在我印象中,这是一个大师式的学者,连周扬都不得不对他的“顽固”网开一面。因而当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孙立川先生和我提起这本书已经出版的时候,我立即问他有没有不学马列这回事,他说有。
买了一本来看,果然。那是1953年他对中国科学院聘请他当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的答复,不但自己不学,而且全所都不学,还要毛泽东和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开证明之事当然不了了之,但是中共中央对于陈寅恪的特殊照顾可见一斑。在反右前粗暴地冒犯了他的党委书记龙潜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在反右期间有人提出要把他划为右派,也遭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拒绝。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60年代初,他的生活破例地得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特批,可以说是全国知识分子中最好的关照。在知识分子中间,他可能是惟一享受到多位中共要人如陈毅、康生、胡乔木、周扬先后登门拜访的殊荣的。后来在他健康状况恶化时,广东省特别为他安排了专职护士;为了方便他在基本失明以后散步,还在他家门前特地修了一条白色的水泥路。
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安然地进行研究长达十余年,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毕竟只有一个陈寅恪。从1926年就在清华国学院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齐名的四大教授毕竟只有他一个留在了新中国。奇怪的是和他一样拒绝了蒋介石接往台湾的飞机票的朱光潜却没能免于思想改造,而他所得到的尊重大大超过了俞平伯、冯友兰、钱钟书。凭良心说,这好像是个奇迹,实际上是他的学术地位得到确认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