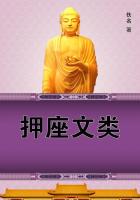却说越女士和秋女士讲论些别后的情形,忽见秋女士身边挂着一柄倭刀,便问他可是在东洋买来的?众人听了,也一齐走来观看。秋女士回答了一声“正是”,便把刀解将下来,抽刀鞘,送与众人看去。又对越女士说道:“小妹以一弱女子身,只身走万里,渡重洋,到海外求学,所赖以自卫的,全亏得这把宝刀呢。况且我生平也没有一个知己,这宝刀清如秋水,凛如严霜,抱革命的宗旨,有流血的本领,侠骨,人不敢犯,杀得人,也能救得人,正和小妹有一般的抱负。所以小妹近来便把他当作个知己,因此上终日和我影形不离的。”越女士笑道:“贤妹好侠负义,果然配用这把宝刀。前次听得你有赠送狱囚使费的一事,真是令人敬佩不遑,真不愧‘鉴湖女侠’的四个字。但是你带了这刀往来重洋,进出内外口岸,那些经过的关口,难道都不来盘查你的么?”秋女士道:“那些卫身的家伙,有什么要紧?外国的文明法律上边,都许人可以自由携带的,没有什么犯禁的道理。不要说小小的一把倭刀,就是七响九响的手枪,也可以带得,这值得什么大惊小怪!”越女士又道:“在国外呢,那倒本来不怕什么。所怕的是我们中国内地的关卡,倘被他们看见了,恐怕就要把贤妹当作革命党了!”
秋女士笑道:“姊姊,怎么你近来的胆子竟如鼷鼠一般的小了!凡事总要讲个实在,不能无凭无证,就把人诬作革命党的。我脑筋里虽也有个革命宗旨,但是我的家庭革命,和他们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是冰炭不相投的。我在东洋,见了那些革命党里的人物,理都不大去理他们的。因为他们这班人,都是些能说不能行的。竟有几个连‘革命’二字也解不清楚,种族的分合是更不懂得,不过随潮附流混个热闹罢了。就是那个徐锡麟,我也嫌他的主义太狭。我和他结交,也不过慕他的一个血心罢了,宗旨是也是各人行各人的。我既没有政治上种族上的革命凭据,那要怕他们做甚?”越女士又正色的答道:“竞雄,你不要这般说。现在外边是世路崎岖,实在危险得很!小心谨饬的人,尚且要被人诬陷,不要说像你这般率直无忌的人了。竞雄妹子啊,我劝你以后总要留心一些,才是道理。”秋女士勉强点了点头,说了一声:“领教。”
正在这当儿,只见一个老妈子进来,说声:“酒席已安排好了,请奶奶们出去用酒罢。”秋女士立起来道:“姊姊何必如此客气!”越女士道:“也没有什么盛席,不过略备水酒一杯,替贤妹洗尘罢了。”秋女士也不谦逊,便一同走到餐室。大家分宾坐下,那两个女学生,同越女士的女儿,也坐在两旁陪席。大家且饮且谈,无非又谈了些东洋学堂里的情形,同日本的风景名胜。不一会酒过数巡,秋女士有些酒酣耳热的态度,忽然间长叹一声的说道:“纵有千杯,只是难消却我胸中的块垒!”说罢,便起身取了把刀,在筵前大舞起来。但见他舞得寒光闪闪,只见刀,不见人,真个是花团锦簇,不让古人。秋女士舞了一回,重又入席,再喝了一盅酒,便向越女士问道:“姊姊,我醉了么?”越女士笑道:“不醉!不醉!这是妹妹素来的豪气如此。况今日久别重逢,理应有这般兴致。”秋女士见越女士赞他有豪气,听了心中更自起劲,便说道:“古来男女侠客,都是使剑的多。我没有宝剑,故就把这宝刀,当作宝剑了。”说着,又见那边摆着一张风琴,便走到那边,坐了下去就踏,嘴里说道:“我有一只宝剑歌,待我来唱与你们听。”一头说毕,一头便按着腔调,且踏且唱起来。越女士和两个学生静悄悄的,听他唱道:
宝剑复宝剑,羞将报私憾。
斩取国人头,写入英雄传。(一解)
女辱咸自杀,男甘作顺民。
斩马剑如售,云何惜此身。(二解)
干将羞莫邪,顽钝保无恙。
咄嗟雌伏俦,休冒英雄状。(三解)
神剑虽挂壁,锋芒世已惊。
中夜发长啸,烈烈如枭鸣。(四解)
歌罢,越女士和两个学生俱叹赏不已。秋女士道:“姊姊,我酒力不胜了,我们大家吃饭罢。”伺候的婆子便盛上饭来。众人吃了,盥漱已毕,秋女士又和众人说了些日本地方的风土情形。看看自鸣钟已到了两点十八分了,于是大家安寝,一宿无话。次日,秋女士一早起身,即往他几个相熟朋友处去,拜望了一天,仍回到曹家渡安歇,一连住了几日。
这日,正在和越女士闲谈些兴学创报的话儿,忽见一个人送了一封书信进来,说是“绍兴来的”。说罢,便回身去了。这里越女士把信拿在手中一看,向秋女士说道:“妹妹,是你府上来的。”秋女士闻说是他家中来的信,便接来拆开一看,不觉“阿呀”了一声,那个眼泪直流的流下来了。越女士见了,便也吃惊道:“什么件事,妹妹便慌张到这样呢?”秋女士哭着说道:“姊姊,我的母亲不好了啊!”越女士听了,也着急的说道:“几、几、几时不好的?”秋女士道:“昨日早上八点钟去世的。我本想在这里再住几天,运动那些稍稍开通的女同胞,凑些资本,创办一个女报馆出来,如今是定要回绍一次了。我打算今天就要动身。”
越女士见他归心如箭,也不强留。当日秋女士随即收拾行李,辞别了众人,直向绍兴进发。一路无话。
这日到了绍兴,秋女士上了岸,叫脚夫挑了行李,一径来到家中。只见墙门大开,里边哭声震耳。秋女士虽是英雄心肠,到此不免也要苦噎咽喉,大哭起来。也不顾亲朋戚族都在这里,他便从大门外头哭起,直哭到里边,跪在灵前,号啕大恸。众亲友见了,也都替他落下泪来。他的哥哥秋裕章,在孝闱里头听见了他妹子的声音,便出来把秋女士搀起,兄妹见面,又大哭了一场。众亲友齐来相劝了一回,不消细说。秋女士走进孝闱,和他嫂子相见过了。
裕章道:“妹妹,我前日得着你一信,知道你东洋已经回来了。只是你为什么不早一日回家?如今母亲不能见面了呢!”秋女士听了,不觉又呜咽起来,说道:“哥哥,我这一番的苦楚,一时也说不尽来。我自东洋动身,到了上海,闻越兰石姊姊说母亲哥嫂都是平安在家,故此我就放下了心,要想在上海干些事业的。谁想起母亲要长别我的呢。我前年出门的时候,母亲以年老多病,不能再见为虑,不料今日果应其言。”说罢,又大哭起来。他的嫂子上来把他劝住了。裕章见他妹子哭得这样的凄惨,不免自己也陪着他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此刻见他妻子来劝,便也收了泪,对秋女士说道:“妹妹,你且去吃些饭再来。”秋女士道:“我这时候也不觉着饿,停一回吃罢。”
正说着,秋女士的女儿并儿子,他两个正在后头玩得起劲,忽听见人说他的母亲回来了,二人连忙跑了出来,叫应了。秋女士见他二人也长了许多出来,便说道:“你二人在那里玩呢?”姊弟两个那里肯实说,支吾了一回,便望他母亲怀里一滚。秋女士一头抚弄着子女,一头向秋裕章问道:“哥哥,母亲的病是几时起的?”裕章道:“是前月起的。我回来的时候,病已着重了。至前日下午,便觉模糊不省得人事。直到半夜过后,才开一声口,后来又不开口了。及至临终的时候,又要了一口茶吃,糊糊涂涂的向吾说道:‘你妹子出洋去了。’我回覆他说:‘已经回来了。’他听见这话,便睁着眼,说道:‘回来了么?怎么不回来呢?’”秋女士听到这里,那个苦块,已噎住在喉咙里了。呆了半晌,才又听得他哥哥说什么“离异了你妹子,你要不好好的养着他,我在地下不瞑目的。”他哥哥尚未说完,已经把个秋女士哭得不像人了。女士的子女,见他母亲这般光景,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一时哭声震地,把个死人几乎要哭醒呢。
外头众亲戚听见了,一齐进来,把秋女士劝住。又有一个人进来,向裕章说道:“外头帐房里有事,请你出去一趟。”裕章答应了一声,跟了那个人去了。这里众人又和秋女士叙了些闲话,并劝他不要过于悲伤了。不一时天又晚了,众亲友也都告辞回去。一宿无话。次日诸事已毕,秋裕章在家守制,这也不消说得。
且说徐锡麟自东洋回来,便在绍兴开办了一个大通学堂,后来又开办了一个明道女学堂。正因这个女教习一时难觅,他便想着秋女士。闻得已经回国,此刻他在家守孝,尚没有事,何不去请他出来,担任这个责任,谅来他也是愿意的。徐锡麟打定了主意,便亲身走到秋女士家中,当面和他商量。果然秋女士一口应允,并不推辞。从此秋女士就在明道女学堂,当了一个教习的责任。后来锡麟到了安徽候补,就把这监督的责任,也卸在秋女士身上去了。好一个有才有学的女士,一身兼了两役。他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只是尽心竭力的,把个明道女学堂办得整整齐齐,女学生便一日多似一日了。这也不在话下。
一日,秋女士作了一篇白话的浅说出来,命名曰《敬告姊妹行》。他做了这篇浅说,就用印字的机器印了二千多张,派人传送出去。一时绍兴城里的乡绅大户,茶坊酒肆,都送到了。
当时作者也在绍兴城里,同了几个朋友在一爿评议居的茶馆里吃茶。看官:这“评议”两字,倒像不配放在茶馆里招牌上的,为什么他们绍兴人提出这个茶馆的招牌来呢?哈哈,原来有个缘故。因为这个茶馆里头的一班茶客,都是那绍兴学会里头的会员。那班会员,无论学会里有事没事,每日定要到这里一次,或议事,或闲谈,这里就是他们的叙话所在。所以人把这爿茶馆,就叫做评议居了。闲言少叙。且说作者那日也接了这篇浅说一看,倒觉得字字有血,句句有泪,实在写得淋漓尽致。令人读了一遍,不由的那股热血,就往上涌将起来。
你道他写的是些什么呢?诸位不嫌讨厌,待我慢慢的想他出来,抄给诸位看看,望诸位见了这种血泪似的浅说,也去念给那些不识字的女子听听,庶几不枉作者抄他的一段工夫了。闲言莫叙,且说他写的是道:
我的最亲最爱的诸位姊姊妹妹呀!我虽是个没有大学问的人,却是个最热心最爱国爱同胞的人。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的进了文明新世界了,智识也长了,见闻也广了,学问也高了,声名是一日一日的进了。这都亏了从前书报的功效!今日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可羡不可羡呢?所以人说书报是最容易开通人的智识的呢。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了。我的二万万女同胞,怎么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底下,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吃的穿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恼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还有那安福尊荣,家资广有的女同胞,一呼百诺,奴仆成群。一出门真个是前呼后拥,荣耀得了不得;在家时颐指气使,阔绰得了不得。自己以为我的命好,前生修到,竟靠着丈夫,有此安享的日子!外人也就啧啧称羡:某太太好命,某太太好福气、好荣耀、好尊贵的赞美。却不晓得他在家里,何尝不是受气受苦的?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的喜怒。试问这些富贵的太太奶奶们,虽然安享,也是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罢咧!总是男子占了主人的地位,女子处了奴隶的地位,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
阿呀,诸位姊妹!天下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诸位姊妹必说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又没有本事,一生荣辱,皆要靠着夫子,任受诸般苦恼,也就无可奈何,委之曰“命也”。这句没志气的话了。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欢迎,在外有朋友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反目口角的事都没有的。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这样美丽文明的世界,你说好不好?
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无非僻处深闺,不能知道外事,又没有书报,足以开化知识思想的。就是有个《女学报》,只出了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如今虽然有个《女子世界报》,然而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的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就要想办一个《中国女报》出来,内中用着文俗两路文字,以便姊妹们的浏览。这也算我为女同胞的一片苦心了。
但是凡办一个报,如经费多了,自然是好办的,如没有钱,未免就有种种为难了。所以我前头想在上海集个万金股本(二十元做一股),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也不枉是个中国的女报了。为二万万女同胞生一生色,也算我们女界不落在人后了。自己能立个基础,后来诸事要便利得多呢。不料我将章程托《中外日报》登了几日,直到今日,没有个人来入股的!唉,照此看来,我们女界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想起来实在是痛心的呢!我说到这里,泪也来了,心也痛了,笔也写不下去了。但这个办报的心,就这样的冷了吗?却又不忍使我最亲最爱的姊姊妹妹们,长埋在这个地狱当中。所以我今朝和血和泪的做出这篇白话浅说来,供我姊妹们的赏阅。天下凡百事体,独力难成,众擎易举。如有热心的姊妹,肯来协助我一助,则中国女界幸甚!中国亦幸甚!
众位,你道绍兴的学界绅界女界,看了他这样痛哭流涕的一段白话,他们应该怎么样的起敬他,帮助他呢?咳,真真是再也想不到的!原来他们看了这段白话,也不去起敬他,也不去帮助他。反有一等顽固的绅士,说他这种言语,实在荒唐得很!若使通国的女人,个个依了他这个心肠,不是我们男人反要被女人压制了么?所以这件事体,断断乎依不得他的呢!
后来,秋女士见仍旧没人来理他一理,他也无可奈何。只是他这副救拔女界的心肠,终不肯冷的。于是就把自己的心血钱,并在几个亲熟姊妹处借些,拼凑拼凑,就托书局里头代印了几册报纸出来。然而没有人去看他的报,他又没接续的经费,将自己拼凑得来几个钱用完了,也只得停止了。从此也没有人去帮助他,他自己又没有力量,遂将这个办报的念头搁了起来。
后来见富太守和他亲近了些,富太守的母亲又爱上了他,将他认做了干女儿,他便和富太守商量,想要把这个报重新整顿起来。争奈绍兴的那些绅士,又极力的撺掇着富太守,不要帮助他。富太守听了绅士的话,也便不答应了。秋女士一番高兴,又落了一个空,从此把这办报的头念丢在脑后,再也不提起了。
直到次年,放过了暑假,不知他怎么的又把那个办报的念头想起来了。不料他正在想这个念头的时候,就被徐锡麟闯了一个叛逆的穷祸出来。官场正在疑着他,只是尚没有定他的罪名。那知一个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有那个专会拍马屁、走乖路、害好人的绅士,又把他告了一个从逆。那个富太守也是个只要自己升官发财保太平,就不问问明白,竟以人的性命,当作杀鸡杀鸭一样。得了这混帐绅士的一个禀帖,就如奉了王命了,在牢监里拿个秋女士绑了出来,押去便杀。咳!真真可惜,秋女士一片热肠,想要把中国女界的睡狮唤醒,不料他大志未偿,为了一个徐锡麟,就白送了一条性命!
女士的哥哥秋裕章,虽然是个男子,争奈他入了官场的人,早把这“革命”二字,怕得比见了阎罗王尤怕。他听见妹子为了革命党死的,便吓得连自己祖宗传下来的那个姓都几乎不要了。虽也晓得他妹子的死是冤枉的,然而终究不肯出头,替他妹子伸伸这口冤气。咳,这个秋裕章的心思,也不过是为着这个官儿舍不得罢了,性命还是第二层呢。这也是官场中人固有的性质,也不必独去责备他的。惟是那些绍兴的绅士,为什么既晓得秋女士的死是冤枉的,也是钳口结舌,噤若寒蝉,独不肯发一句公论出来?这也是有关国家大局的事呀,不是专为着秋女士一人的冤枉呢!
倒是那班小百姓心里,还有些公是公非。听得人说明道女学堂的女监督秋瑾是被富太守冤枉杀的,便都鸣起不平来了。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一时聚了无数的小百姓,议论得要和富太守问个杀秋女士的缘故出来。当时又有一个本地绅士,听见说百姓不服起来了,便连忙三脚两步飞跑到华(府)衙门里,和富太守说了。富太守听了,一时也没了主意。还是那个刑名老夫子,肚里的鬼计策倒也很多。他听了这话,便冷笑了一声,走到富太守身边,附耳了一回。只见富太守顿时笑逐颜开,不似先前那副丧家犬的样子了。
究竟老夫子说的是什么话,且看下回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