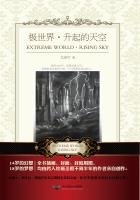文/丁宗皓
对郎雨泽的这本书,私底下我还有一份好奇,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写了那么多的诗文。那些诗文里,承载了哪些内容?这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美国的文化学家迪克斯坦在所著《伊甸园之门》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精神背景,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浸淫其中,都要受到影响,在精神上都会呈现出共同的特征,这个观点支持他对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进行过一次全景式的扫瞄。
几年前,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把一位非常年轻的中国女作家作为封面人物,当然这么做不是基于文学成就,而是把她看成一代新人,独立于传统文化以外,孤独、桀骜、叛逆。这种选择的眼光与视角也是迪克斯坦式的,想必周刊的选家们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在文化交流和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新人必然从传统社会中被催生出来。
这些年里,我们也注意到了,曾经稳定的传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多种文化因素在不同人群中的投射,以及对不同群体的文化塑造,比如在作家群体里,三十、四十、五十以及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文化上并没有呈现出那么鲜明的差异,而70一代、80一代,以及80后这三个年代出生的作家却不断被贴上年龄或者是他们所生长年代的标签。
有人会认为这种分类十分牵强,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同样不可忽视--这使人注意到,迪克斯坦式的划分倒是十分合理,因为,文化对生命的投射似乎是命运的一个部分,会在很短时间内,对人群进行复制,这种复制是不知不觉的,方式也很简单,即通过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来完成。
我尽量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浏览这个男孩子的文字,可以说还有那么几分小心和神圣,仿佛正在从一个沉睡的孩子身边经过,看见他在梦中微笑,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而笑,所以更不能惊扰。
但是,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自己的文字里,勾画出了一个他这个年龄的人所生活的现代空间,互联网、博客、他国、外省等。近日和少研闲聊的时候谈起过类似问题,比如生活的空间感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以我个人的体会,举一个例子,比如在我和我同龄人的观念里,除了家乡诸如乡、县城、市以外,其他地方都是异乡,而在精神上,异乡都意味这流离之所。而在这个孩子的文字里,我们观念中的空间已经被放大了许多,世人常常慨叹世界变小了,但实际上,是人的空间感变大了。
除了交通、通讯等因素以外,大众文化成为这一代人精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诗文里,流行元素不断出现,安妮宝贝等符号被提及,流行歌曲在他诗歌叙述过程不断闯入。显然这个男孩子了解当下诗与歌的分野,而要彻底拒绝干扰还需要时间,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这些成人细细地揣摩,并考量他们所依赖的文化环境蕴藏着多少我们忽视的因素。
浏览这些诗文,越来越多的欣喜来到我的心中,这十分意外。我记得自己在中学时代乃至大学学习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传统,除了古典诗歌以外,离自己最近的,是惠特曼、聂鲁达、郭小川、艾青等等。而在这个孩子的文字里,北岛、顾城、舒婷、海子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当然真正的传统远远不止这些。
我的意外和欣喜在于,真挚和真诚的诗歌写作,代表着两个向度,一个是纵向的对于历史和文学传统的回溯,另外一个向度,是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精神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被物质生活的贫或富所遮蔽,当然也不被时尚中涌动的人流所牵绊。
显然,郎雨泽的文字里,同时表露了这两个向度。而后者是通过与他这个年龄不十分相符的孤独和忧伤表现出来的。生命到这个年龄段里,"少年愁"是自然发生的现象,但是,大众文化所特有的欢乐品质以及时代"往下笨"的走向,足以覆盖并抚慰这颗小小的心灵。我的欣喜还在于,这份孤独感和小小的忧伤还在,因为有思想和诗意的心灵都是忧伤的,忧伤涵养了一份可贵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所以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句子:"不,我从不被谁记起/所以也不会被人忘记"
我无从想象,这样一个小男孩,他的生命已经被诗歌打开,他的未来是怎样的?会不会继续写下去?而长大以后,又会怎样看待中学时代的这些文字,以及我写的这个煞有介事的序言。我只能说,诗歌乃至其它文学门类,是人面对这个世界的精神方法之一,它能够带给人的,是一种不可能广为人知、更没人能与你分享的幸福,因为,这是一种独自的精神历险。
而最后要说的,是一份祝愿。
(作者系辽宁日报传媒集团编委、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