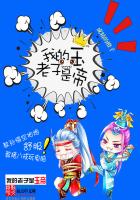在越达公司一排高高耸立的办公大楼后面,如茵大草坪旁边的一长廊的葡萄架里头,穿着普通衬衣,敞开着衣领的冯登科,靠坐在长廊一侧的窗棱似的石框上。他的双手放在弯曲起的右腿的膝盖上,把因失神而呆滞的目光投放于稍远的,复盖着层层叠叠藤蔓,及一片油亮绿叶的水泥樑架之间。他久久地看着那些,在藤蔓与藤蔓重重缠绕之下,一串串密密地垂吊着的,虽默不作声,却是“情趣盎然”地随风摇荡着的,紫白两色混于一体的小花朵们。
而在长廊的另一头,衣着整齐的江海岭,因春末夏初时的那种闷热感,使他焦躁不安地在廊下来来回回的走动着。当闷热空间中突然吹来一阵凉快的清风,把他胸前的紫红色领带飘扬起时,向上推一下眼镜的江海岭,为有风飒然而至,感受到了快风的舒坦,即也想呼叫起“快哉此风!”并随之想到,“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这两句话。心想:风,尚且由于所依的环境不同,其势也就不同,今后我做事,怎可不由状况的不同,而为随机应变,即随风转舵的呢!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为受到了一时凉风之快而觉爽朗的江海岭,接着,又轻声默读了几句有感而发的《风赋》中的句子。
随后,江海岭慢慢的踱步到长廊的那一头,来到了冯登科面前,瞧着他,经飞快地思索,再需要明确一下地问:“冯书记,上星期的评估会是怎么评估的?评估结果究竟是对谁有利?”
对江海岭的所问,冯登科没有立即作答。在放下右腿,目光脱离,开满一片紫藤花的紫白色的樑架后,若有所思地沉闷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回答道:
“在下一步将由谁来领导我们公司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上,我是很明白,也是很坚决的。因为,木不可离根,离根则枯;水不能脱源,脱源则竭。万一,如果让高原真的当上了总经理,那还了得!我们以往和今后的所得利益不保不去说,弄不好,我们还会被他们拔出了萝卜,翻了坑,被兜底挖的呀!每想到这种情景的出现,我手心里就满手是汗!海岭,我们一定要从长计议,我们总得有个阻挡他们的办法啊!”说这话时,冯登科眼里是充满着焦灼,脸上堆积着忧愁。而江海岭左手臂支着腰,右手捏住衬衣第二粒钮扣处,还在连连地煽起点风,好使身上感到清凉些。同时,他看着冯登科的脸色,不断地点着头,应承地发出深切理解的认同声:
“唔,唔。是的,是的,一旦被他们抓到把柄,是太可怕了!是一定要有个办法的!是一定要有个办法的呀!”江海岭说着,又慢慢踱步到长廊的另一头,大概是为刚才所讲的一定要有个办法,而去思考一定要有个什么样的办法吧。
谈到事情的可怕之处,于沉默中又去望着连绵地,一串串密密垂吊着的紫白色的小花朵时,这下,完全出了神的冯登科,看着看着,觉得这些小花朵们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后,开始像动画般的旋转地舞动,慢慢地,还错综相涌,继而汇流地团聚集合在一起,而后再孔雀开屏似的伸展开来,这时,显现在冯登科面前的,已不再是紫白色的紫藤花,而是满眼的几何花纹和印影着的头象,接着它们又铺展开去,可见层层叠叠,厚厚实实的绵延体,这是——手握5千9百万元的账单而想象出,可平摆厚铺起的,用人民币筑成的钱的城墙哦,并且都是自己确确实实拥有着的,完全属于自己可支配的钱哪!!
提起此事的来龙去脉,那需从好多年之前说起:
那时,乘发展市场经济之势,进入新一阶段的深化改革还在摸索之际,权利又没有相应的体制作严密的监督之间,冯登科安排江海岭,任越达公司驻TJ办事处主任一职时,在冯登科的怂恿,甚至于就是直接与其合谋之下,用公司提供的发票、办事处的帐号、公司经营的合法票证,狠一狠心,截留地巧取豪夺了越达公司驻TJ办事处一期多的全部销售款,共计,5千9百余万元。
在此其间,冯登科与江海岭,还曾经利用澳国神鸟集团想和越达公司谈判合资发展的机会,以神鸟集团投资300万至1亿美元的假名义,再分别与一些省市的九家单位,签订过《中澳合作意向书》、《国际商业借款合同书》、《中外企业合作合同》,然后请SH的一家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高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项目评估,先后,还诈骗了翻译费、评估费、手续费、论证费、前期费,还有其它凡能想得出,编得出,且说得过去的种种巧立名目的费用,共计580万元。就用这些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他们两人穷奢极欲地买房、买车、买家具,及用于私人投资和投入股市,包括自己家庭生活中的无度挥霍,与外出旅行时豪爽地购物,这可都从来是只管用,不必算的。他们还曾一起感叹过——,再努力一把,以后,买架私人飞机飞飞,或者,买艘皇家豪华游艇游游,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天堂生活啊!当然,在梦求大富大贵之前,早就准备好这样的事——
如此之大的缺口,总必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既然早有如此预见,冯登科便与江海岭以建立一项所谓的新项目为由,从策动、谋划、实施,推进这件事的一开始起,就先已同步地设计好刁钻狠毒,又聪明极其的金蝉脱壳之计。他们看准那个,只会凭一般的日常工作经验开展工作,对工作中的新问题,从不求深入认识经济运动的规律,但却好于骄奢淫逸,贪婪腐化至极,且不怕贪赃枉法,常常还显得稀里糊涂的总经理,用移花接木、一词多解、张冠李戴、含含糊糊、利令智昏,等等等等的手段,总之,祖传的三十六计,能用的都用上,又是哄、又是瞒、又是骗、又是诱、有时还近似于逼迫地,让他在完全由江海岭出面提出,冯登科只是意向地表示口头支持的几份设想框架、方案确定、计划推进、补充规定、资金追加、合理报损,等等等等的相关报告、申请、审核及批准上,或要求,或提示地请这位总经理,作出首肯性的指导和批文,以及签字盖章。最后,当然终于汇集成,有确凿证据可证,这项新项目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总经理直接的策动,谋划、领导与指导之下进行的。如此之后,一待暴露,不费口舌便可引使人们自然地理解:这些事不是都在总经理的直接谋划,领导和指导之下发生的吗?事情能做到这个地步,没有受总经理的指使,怂恿与共谋,他们俩怎么可能做得成?从而使这个法人代表,最终终于成了应负这些事的首当法律责任人,且是到了有口难辩,就是跳到长江里去也难以洗刷得清的地步。
事情就这么一步步地进行着,深入着、发展着,也真如精确计算到的那样,那么大的销售缺口,怎么可能瞒天过海,不使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必然的揭露,果然来临了!在某一天,追查才刚开始,暂还没正式立案,只是上级领导跟这位总经理谈了几次话,这位总经理就沉不住气了。他因不能为非自己的真实指导思想部分,及其多项财产的来源作无罪的有力举证,以及,在一些员工的冷眼冷语,及告知将难逃转入司法程序的惶恐下,尤其是为了这件事,家人与他不知怎么地,连续发生了二、三次极其激烈的争吵,终于,在难平心头之怒,难息满怀之怨,于万箭穿心般的难受之间,一时绝望得太冲动中,乘月黑风高的深夜,全家深眠熟睡之时,留了匆匆写下想说明,却并没有能够说明问题的遗言,悄悄来到离家不太远处的桥上,“扑嗵”一声,投河自尽,竟糊里糊涂地以死,这样的生命的代价来极力表明——自己虽很贪婪,很腐化,但其中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冤屈要申诉!!
总经理的冤屈之死,一开始使冯登科与江海岭非常的震惊,这种隐蔽自己,嫁祸于人,使自己的良心也有过一点的呵责。但很快,两人就暗自庆幸,欢呼起来,这真是太好了的结果!因为,人既已死,不可追究,他们也即跟着逃过了鬼门关。当然,作为连带责任人,受查办也是必然的,但隐匿掉大宗的核心证据与确切数据,再往死人身上一推,来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是,就是神仙也会一筹莫展,无可奈何的呀。而后,虽为此也受了严重处置,但这与暗藏的丰厚利益比,简直又算得了什么呢?是的,是也有像何以然及沙老那样睿智的人,暗底里曾怀疑过他们有栽赃与隐匿的嫌疑,然而凭着他们两人缜密地逻辑推理,深谋远虑的巧妙安排,会给人留下很容易把握到的蛛丝马迹的么?嫌疑毕竟是嫌疑,就让何以然他们等等的一些人,坚信不疑地嫌疑下去吧。质疑要有证据;分析要靠证据;定义要以证据;指控要依证据;结论也要凭证据,毫无可证的证据,只得无奈又无奈,能把我怎么样?!但是,现在使自己焦虑不安的是,如果让高原与何以然他们这样更有头脑,思辨十分清晰的人做了总经理,能始终不发现问题所在?!一旦顺着蛛丝马迹发现了问题的依据,他们报上级进行再追查起来,到时,万一真拿出了意想不到的资料,或证据,其后果必是阶下囚啊!……,那真叫人可大惊失色,不堪设想的啊!而且,还有那个沙力的父亲,冯登科与他,从早期的共谋国企改革之始,就多次以他的名义,在发展资金中人不知鬼不觉地为自己截留过八万元的钱。后来,毕竟是少量的截留,便在改革需要付学费为由的呼声中,由沙力的父亲为主,一起出面作过几次解释,最终才算是以“改革需要付学费”的名义闯过了这个肃贪关。如今,要是,万一,这些匿迹将根连根,株牵株地一起都被接连地深挖出来,那……,那……,那……,那……,这事真叫人如坐针毡,也将是坐以待毙的哟!
“冯书记,上星期的评估会究竟是怎么评估的?”不知何时,江海岭又踱回到了冯登科的面前,似有联想地再次问起,这才使冯登科的思绪,一下惊回到了现实环境中来。他定一定神,此刻看到的,依然是水泥樑架间一层层缠缠绕绕的藤蔓,及一串串,密密垂吊着的紫白色的小花朵,仍在“情趣盎然”地随风摇曳着。只是觉得,自己心中也有着缠缠绕绕的藤蔓,及与,紫白色小花朵相同地摇曳着的恍惚的神思。
许是气温高,叫人确感很热,或者心里有着一股很不安的焦灼感,冯登科不禁也站立起来,开始在廊下来回地踱步了,并回应江海岭的问话:
“这次会议啊,就是人气风向标。无需隐讳,评估会上,看来,何以然与高原,他们俩已经给相当一些人留下了良好的影响,极可能成为这次首肯的人选。当时,要不是由于我谈出了一些的道理来,才勉强改变了最后的影响力度,他们俩就已经是不二的人选了哦!”
“是嘛?!啊——,毕竟老马识途呵,书记,你毕竟是很有经验,很善于谋划的诺。”江海岭推了推眼镜,似笑非笑的,半是奉承半是应从地作着赞许。
“不,这种改变不在于经验和谋划,而是得到了四个以前我曾恩赐过他们的人也在场的支持。如果那四个人不在场,或者有再多的人参加会议呢?那我将会显得既无力,也无奈。因此,这次我能影响会议,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由此,我在想,以后怎么办才好呢?”冯登科言由心出,同时深心地表达了十分不安的心情。
“以后怎么办才好?我们只有拼死把沙力推上去,让他也来做只替罪羊啰!”此话,江海岭说得很是轻巧,这下,在他脸上浮现出的,是一种诡异的微笑。
一提到沙力,冯登科也想到了他,急忙说:
“噯,是呀,是呀。呕——,说到沙力,海岭,你打电话叫他马上赶过来。如果我们要做好下一步的事,对他,看来免不了,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做些开导和稳定人心工作的呀。”
“他已经来了。”江海岭迅速答道。
江海岭的告知,叫冯登科甚感惊讶:“咦——,今天是双休日,他怎么会来的?”
“今天,你叫我到这里来商量什么事还需要问的吗?既然如此,少不了终究还是要他来的么,因此我早就叫他到了。现在,我叫他在办公室里准备一些资料,以后,一旦到了需要打法律的擦边球时,这些资料对我们会很有用的,这样,我们心里就仍然可以底气十足的了。”
“啊——,打法律的擦边球?!啊呀!啊呀!海岭哪,这种事我怎么想也想不到的哦!!”冯登科这么说时,用手掌连连拍着自己的前额,“哦!这事我怎么就是想不到喔!海岭,我还没想到的事,你却已经在做充分的准备了哦!思虑缜密,深谋远虑,聪明能干,很有一手的,真还是你呀!”听江海岭如此说,使冯登科不由得感到震惊,紧接着发出了他对江海岭由衷的赞叹,真实的钦佩和倾心的赏识。
“有道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江海岭若有所思地低着头轻说道。随之,摸出手机给沙力发了个叫他到这里来的短信。
心中还在对江海岭赞赏不已的冯登科,望着他,深感此言极是,便亲切地用手搭在江海岭的肩头:
“海岭哪,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做吧。仍然把沙力当作我们的探路棒,让他继续走在前面,你跟着他走,他能走多远你跟着走多远。在这个过程中他犯错,他不行,我们吸取教训后,我会想办法让你接替上去的。他要不出错的话,我们就借着他,也总结总结经验,不断地揣度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通过看透事情来把握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什么时候,可以再也不需要他了,在党委会,我会看准转折的机会,以他不是人才,或者是没有上乘表现为由,再来推荐你。我要怎么做,自有强有力的关系网来支撑我,在投票上,你就尽管放心好了。沙力,哎,哎,沙力这个人有什么用!他就像田里的蚯蚓一样,钻倒是蛮会钻的,可是肚子里什么货色都没有,只有一肚子的烂泥巴。他怎么能跟你比的啊!哎,哎。”
“冯书记,你话虽然是这么讲,其实我心里是很明白的。”此刻,江海岭确定,就顺着他的这句话,把自己心里头早在疑虑着的预感,就当着他的面实说出来,看他怎么个没有退路。于是向上推了推眼镜,即继续说道:“冯书记,其实,你嘴上虽这么说,但你真正想要的,还不是就让沙力来当这个总经理!毋庸讳言,因为你觉得你控制他,比控制我要来得更容易一些。对我们两个人,在目前,你是两边都利用,是各取所需呀。但,尽管如此,像以前一样,我什么时候都决不做出会让你担心的事,这是我对你的保证。我的话从来都是真的,是算数的,因为,利害关系迫使我们只能够如此的啊!”江海岭说完,又推了推眼镜,虽咧嘴在笑,然而,不经意地瞬间射来的鹰隼似的目光,叫冯登科看了,直感到了一种阴冷,甚至于是不寒而栗。
实在意料不到,对自己一直以为编织得深藏不露,天衣无缝的心理,江海岭他怎么竟然能这么准确看透自己,还讲得是这么的直截了当,且入木三分,真意外得,不能不使自己非常的吃惊,不得不叫自己极其地愕然,这几句话像刺到了自己的心脏一样,使冯登科感觉到了一种剧痛。他瞪着眼,张着嘴,下意识地用手掌轻按在自己的胸口,一时,又因突然,而惊讶得不知再怎么往下说好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把,哦!!你是这样想的?!你呀……。这一句半话说出了口。
而江海岭却仍若无其事地慢悠悠的笑说道:
“但是,冯书记,你尽可放心,我是很懂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该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好发挥智慧的程度和时机的哟。我决不学杨修,聪明得把自己的命也聪明掉了,因此,说到底他其实还是不聪明的。我想你也不会学那曹操的容忍度的。否则对你,对我,对我们两个都绝无好下场的哟!这是显而见的吧,今天,把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十分明确地跟你摊了牌,可说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哦,以后还有什么想法我们就来个心照不宣吧。您意下如何?”
冯登科又一次被江海岭的这几句话深深地震慑住了,于是,像重新认识到了这个忘年交的真性情,便跨上二步,一把紧握住江海岭的手,富有感情地连连说着:
“好,好。海岭,海岭哪,你既然把话说开了,也说到底了,索性这样挑明了也好,也好!很好,非常好!你让我知道了你有这个担忧,我心里都有数就是了。是的,是的,你不学杨修,我,我也不学曹操,我们之间万万不能互相地猜疑,要小心,祸起于萧墙之内呵!你讲得对,你讲得很对,是利害关系迫使我们只能紧紧地抱团在一起了,现在情况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哦!!”
“冯书记,你既然知道了我有这个担忧,以后会不会因此,就把我刚才说的事,做得更加的隐蔽啊?”思虑上严丝密缝的江海岭,仍然没有疏忽,他对冯登科紧逼一步地作了这样的质疑,其实,也在暗示冯登科断绝有这样的打算,如果万一会有的话。
江海岭的话,使冯登科先是愣了一愣,接着赶快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利益和命运的捆绑已不容许我糊涂了。RB的相扑赛,为什么要赤身裸体?是为了表示相互不藏暗器。我们俩知根知底,也已经像是赤身裸体一样的了,再怎么藏得了暗器呢?你说是吗?”
江海岭听冯登科所言,像是放心地重重点了点头后,把两手插在裤袋口,又从长廊的这一头漫步到那一头,在再折回到将近半程的长廊时,虚见远处的树荫缝隙间,已有个闪闪烁烁的人影在快速移动,即头也不抬起地,伸起手臂指给冯登科看,说声:书记,你看,他来了,来得还算快的哦!
随着江海岭的指说,冯登科急忙抬头看,见整件衣衫敞开着,还露出了内穿着的,有点汗渍的背心,剃着板刷头的沙力,已经兴致勃勃,急急忙忙地来到了自己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