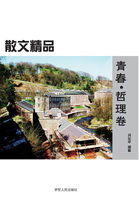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都是帆布书包,清一色的双星球鞋,刷了一次又一次,只刷到蓝里泛着白,白里晕染了黄。永远都是可以想到的几本课外书:除却《青年近卫军》,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除却《三国演义》,就是《聊斋志异》,只有几个“进步人士”才会读读汪国真,谈一谈戴望舒。
正是老狼的《同桌的你》风靡校园的时候,这样的歌,多少要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要激进一些,能激化一下我们懵懂的情愫,让我们在青春的暗夜里写着蠢蠢欲动的诗,多美妙的小心思呀!直至后来《栀子花开》、《那些花儿》之类的校园歌曲出来以后,也没有压过当时的感觉多少。
那是校园民谣的时代,也是人心挣脱拘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全社会都是校园,所有的先锋派都是从校园开始的,最终在社会里被无限地放大。
那也是吉他风行的时代,谁若能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留一头稍稍长一些的发,肩上扛着一只吉他,再能在球场上蹦跶那么几下,一定会吸引不少同学们的眼球。
那也是诗歌的年代,除了我谈到的徐志摩、戴望舒、汪国真,当然也少不了顾城、海子、北岛……谁能写得一首好诗,再配上庞中华一样硬朗的钢笔字,简直堪称校园明星。
那个时期的教辅资料还没有满天飞,各种周末补习班还没有盛行,校园,成了最美好最肆无忌惮的乐园,那里的每一处橱窗前和教室里也播撒着我们如诗一样的光阴。那个时期的梦呓最甜,没有梦魇,那个时期的关系最好处,没有青白眼。那个时期的你我都纯净得像山间的小溪水,哗啦啦地在岁月的河道里流淌着,还唱着青春里最美的诗……
针尖上的蜂蜜
爱真是个简单的物件。被人说到了烂,说落到了底儿掉,穿越蛮荒,穿越时光隧道,现代人还在说。
随意翻开一部电影,一部连续剧,一本小说,如果找不到“我爱你”的影子,那这电影电视剧小说是失败透顶的。因为,他(她)连爱都不要了,哪位观众、读者愿意要他(她)?
一家晚报采访我,问我写了这么多和这座城市有关的文章,缘由是什么?
我说,只有一个字——爱。
太煽情了吧!记者说。
是的,生活就需要煽情,我们所处的生活在工业化的侵蚀下,到处都显得干巴巴的,太需要两滴眼泪来洗刷一下枯燥了。我如是答。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是《大话西游》里的台词。
爱一座城市需要理由吗?这个世界,若是凡事都需要理由,我们或许将要寸步难行了,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心中最隐秘、最柔软的情结,一切理由都是惨白的。
我读雷平阳的诗,《亲人》,写得真有趣,也真的耐人寻味——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
是的,所有的爱都是偏执的,爱不偏执,便不是真爱,爱偏执,爱才爱的值。连爱都不偏执了,要爱作甚?
爱到狭隘。爱本身就是狭小的,一对一的,定点接收的,撒网叫什么爱,那是渔猎,得到的是欲望的渔利,而不是同样爱在你的心灵。
我在冰雹之后来到树林,看到了被冰雹砸掉了底儿的鸟巢,一直血毛娃子小鸟掉了下来,并不大碍,而它的父母却在枝端惊心地叫着,似在滴血。
我冒着摔跤的危险爬到满是雨水和青苔的树上,用草给鸟补好窝,把刚才那只小鸟娃子放了进去。不为别的,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如果那只小鸟是我,而站在树梢上的是我的母亲,她该怎样忧心如焚?
爱像是针尖上的蜂蜜,疼且甜着,即便是针尖上这么丁点儿的地盘,也是可以用来传递的,在针尖和针尖之间,搭一座浓情蜜意的桥。
珍重青春
两年前,在上海某书城里,有个名叫单海海的作家正在搞签售,书名是《穿行都市》,悬念推理小说,正是我喜欢看的那一种。于是,我慌忙挤上前去,喷绘背景下,有个戴墨镜的年轻人在签售,估计比我还要小几岁,食指上戴着翡翠戒指,很扎眼。
我终于挤到了作者面前,捧着书,打开签名页说,请老师您给俺签个名留念。
作家很爽快,单海海在扉页上笔走龙蛇,很快就签好了,我拿在手里一看:你小子这么快就把我给忘记了!单海海。
我迟疑地望着他,他去掉了眼镜,我定神一看,这不是王浩吗?
我上去捅了他一拳,怎么是你小子,也写起书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在上海也能遇见你。我做出版业已经三年了,闲时间写写东西,中午别慌走,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好聊聊。
我点头答应。边翻书边在大厅里等,脑海里瞬间想起大学时的王浩,喜欢泡网吧,追女孩子,经常因请女孩子吃饭花光了钱而不得不周三以后吃方便面。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了家乡一家电视台工作,做编导,后来倒腾了两年以后,就到上海卖冷鲜肉去了。
也就是在他卖冷鲜肉的那些日子,写了几篇都市气息很浓厚的小说给我看,故事很好,只是不健康的内容很多,给我这种老传统看,是“惨不忍睹”的。
2005年前的一个秋天,他曾打电话问我借过1000块钱,后来,我总怕这小子又在外面和女孩子们厮混,没有给他,后来他再打我电话,我就关机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
直到今天我再偶遇他,他像是换了另一个自己。中午留我吃饭畅谈,看到他的热情,我总想起多年前自己为了不借钱给他,拒接他电话的事情。
于是,大厅做了不到十分钟,我就逃了。
午饭的时候,接到王浩的电话,他问我,你怎么招呼不打就走了,上次在你那拿的1000块钱还没还你呢?
1000块钱?我并没有借你钱呀!
你忘了,多年前,我手头紧张,问你借的,你很爽快就打给了我。
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对吧?当时我没有借给你呀!你真别生气,我也有苦衷,我当时刚买了房子……
你小子别再狡辩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现在不差钱,你不用接济我,给我说,现在在哪,我把钱给你送去。
我真是蒙了,再也回忆,确认我当时真的没有借钱给他。就匆匆关了机。
一周后,我到单位,收到一张汇款单,1000元,还有王浩先前出的两本签名书,正正规规地签着名字:王浩(单海海)。签名上方还写着一句话:问了好多人,总算找你的地址,永远记得陪我走过青春的好朋友。
我费了好大劲,终于找到王浩多年前的QQ,早已废弃,在他多年前的日志里发现了一篇令人冒汗的日记:借了好几个人的钱,都没音讯了,这个周末好难过,估计他们各有各的忙处,悲惨青春,挨饿写小说去……
这才明白,王浩是故意给我打马虎眼,不想让我难堪罢了,目的是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我没有拒领他的1000元,我带着对他的愧疚收下了钱,什么也没说,但那1000元钱,我一直放在红包里,至今不曾动分文。
又一年后,我收到王浩的新书《珍重青春》。这个书名,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
蜘蛛人距离杂技演员有多远
我认识巷口那位修鞋的老头,他每天都不开心,帮人修鞋的时候也常常咳声叹气。有时候,挺贵的一双鞋,被他在叹气声里一捣鼓,不是线走歪了,就是胶水粘多了,免不了的口角,碰见难缠的主儿,还得陪人家皮鞋钱。
有一次,我修鞋时到他的鞋摊儿。他一边帮我修着鞋,一边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在皮鞋厂工作过,我所在的那个鞋厂能制作各种各样时髦的鞋子。那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厂里一个皮鞋设计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工资就是我们工人的10倍还多。我经常见他吃着猪肉炖粉条,或是抽着古巴雪茄在稿纸上画图。我曾给他学过一阵子,还帮他设计过几款鞋子呢,只可惜学艺不深,设计失败了一款鞋子,给厂里造成了巨大损失,后来我和那个皮鞋设计师双双被解职。要不然,你们现在穿的这么多鞋子也应该有出自我的手笔呢!可惜呀,唉……
原来,这老头怀里揣着一颗皮鞋设计师的心,做的却是打鞋掌的活儿,难怪忿忿不平。然而,转念一想,这样做有用吗,鞋还是要修,日子还要照过,他充其量也就在巷口摆摊,其他地界儿就要被城管赶走。
有人说,这是命运。所谓命运,关键在“运”,好命,其实往往也就那么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在恰当的时间做对了恰当的事情或抉择,仅此而已。若是这些我们都没能赶得上,安分守己地乐享当下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活得悠然自在,无拘无束,这也就等于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好命,或者说是迎来了好命运的第二个春天。
看村上春树的《东京奇谭集》,内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女子,每天被人用一根绳子绑在吊篮上,然后顺着摩天大楼的玻璃外层放下去,她一手拿着刷子,蘸着水去清洗大楼的玻璃,而谁也不知道,其实,她的梦想是做一名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她的梦想和现实虽都把自己置身在差不多的高度,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却有着天渊之别。没办法,她不能撂挑子不干,去学走钢丝,生计需要,她只能一边做着城市“蜘蛛人”,一边做着杂技演员的梦。
其实,这样也好,“蜘蛛人”的工作以喂饱她的“胃”;杂技演员的梦想以灌溉她的“志”,抓住了结结实实的当下,还用那个前方招摇的未来给自己取暖,谁能说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就一定要比做吊篮的大楼清洗工要幸福呢?
杜·罗休弗克说:“不论人生多不幸,聪明的人总会从中获得一点益处;不论人生多幸福,愚蠢的人总觉得无限悲哀。”更何况,我们往往还没有达到“不幸”的地步呢?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有时候只是一张窗户纸的距离。这扇窗,就是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