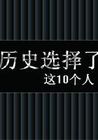道教的宗派分为符箓、丹鼎两大系统。
符箓一系主要源於古代巫术,以传行符箓科仪为主,斋醮祈禳为事,兼言练养成仙。
汉末,先后有张陵开创五斗米道与张角之太平道。太平道因发动黄巾起义失败而绝嗣,五斗米道一支传衍至今,为符箓一系之主流。
至唐宋,五斗米道流衍为龙虎山正一道,净明、清微、神霄等新符箓道派相继诞生,互相交参。自南宋末起,符箓诸派一统于正一天师,汇归而为正一派,其下分支以数十计。
而其中最为神秘的就属流民教,它们源自中国南方,以符箓为主要修练方术,乃从传统符箓派衍化出来,不过却大大不同。
世人都当流民教已经失传,当世没有流民教了。其实还有,问我怎么知道还有流民教?嘿嘿,因为我就是那个流民教当代掌教青峰道人唯一的徒弟——李是非。
我是名孤儿,从小就被师父收养,我们生活在南方一处偏僻的小村庄,今年我十八岁,在这十八年中,除了重要事情外,每天都会随着师父学画符。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一听师父醒来念这诗,不禁一翻白眼,这老东西,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却让我天不亮就起来练画符,太没有人性了。
“是非,是非。”师父在屋内大声嚷道。
“来了,来了,师父叫徒儿有何吩咐?”我虽然暗地里对这老东西没日没夜的逼我练画符很是不满,但表面却对他恭恭敬敬,这老东西虽然平时有些不着调,但一身法力却着实高深。
我推门进去,就见师父穿着那件邋里邋遢的道服,头发散乱,肮脏的手指正夹住我早上做好的大饼在啃。
“今天画符练得怎么样了?”他继续啃着大饼,一双三角眼却斜视着我、
“嗯,今天五雷护身符画了五张,镇邪安家符画了十张。”我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唉。”师父叹了一口气,枯黄的老脸露出不满意的表情,“这样不行啊,还的下苦工,你已经十八岁了,为师十八岁已经能虚空凝指画符了。你啊,嗯,还得下苦工。”
我看了眼自吹自擂的老东西,嘴里道:“师父,你上次不是说虚空凝指画符在二十一岁才学会的吗?”
师父明显不晓得我怎么知道他是在二十一岁才学会虚空凝指画符,表情有些尴尬,但仍旧强撑着道:“胡说,为师明明是十八岁学会虚空凝指画符的。”
这老东西还真会装,上回他在村长家喝喜酒喝醉了,才酒后出真言说他是二十一岁学会虚空凝指画符的。
我正要揭穿他,门外就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二十岁左右粗壮青年跑了进来,他一进来便对师父喊道:“青峰道长,不好了,不好了。”
我一看来人,却是村长的儿子大牛,大牛此时气喘吁吁,脸上汗水滚落,一脸焦急的模样。
我正要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大牛已经拉着师父就向外跑,同时嘴里喊道:“福伯撞邪了,我爹让我请道长去看看。”
“知道了,知道了,不就是撞邪吗!有何大惊小怪的,是非,你准备好东西也过来。”
我一听,连忙拿起平常驱邪用的东西随着师父和大牛向村里跑去。
因为我和师父不与村民住在一起,而是住在村外山脚下,离村里有几里路。等我们来到村里福伯家门口时,发现门口站满了村民,一个个向里张望。
他们一见我们来了,连忙闪出一条道。此时一名长相普通的老者走了出来,他正是村长,村长焦急万分的正要说什么,师父却拦住他,道:“还是先看看福伯吧。”
福伯今天六十多岁,无儿无女,和他老婆福婶住在一起,走进去就见福婶正在痛哭流涕,而房间床上一名老者正躺在那里。
师父一见,就对我点头,“是非,去看看。”
我走到福伯跟前,就见福伯脸色苍白无比,而印堂却发黑,手足抽搐,口出白沫。我一皱眉头,手指伸出翻了翻福伯的眼皮,福伯双眼发直,直愣愣的看着我。
“福伯这样多久了?”我一皱眉头,转身问福婶道。
“今天他像往常一样出去捡牛屎,我在家准备早饭,可不久他就像发疯一般大喊大叫的回来了,回来后往床上一躺然后就成这样了。”福婶一边擦眼泪,一边叙述道。
捡牛屎是乡下人捡了牛屎,然后把其同稻草糊在墙外壁上,等它风干后可以替代煤炭烧锅煮饭,很是经济,所以乡下人一般很早就出来捡牛屎,否则就让别人捡去了。
“青峰道长,是非,福伯到底怎么了?真是撞邪了吗?有的治吗?”村长焦急的问道。
“撞邪是肯定的了,他的魂魄已经被吓得离体,得给他招魂。”我淡淡的道。
一直在旁边没有插手的师父扫了福伯一眼,然后微微一点头,显然和我想法一样,他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道:“是非,这里就交给你了,为师得回去补个回笼觉,刚才没有睡好。”
我一听师父言语,不禁暗自诽谤:这老东西,真会知道享福。
旁边村长见师父要离开,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师父却明白的对他摆摆手,“这里有是非就行了。”说着便扬长而去。
我等师父离开后,就让大牛盛满一碗白米,然后又让福婶去取福伯平常所穿衣服一件。
在我正准备施法时,就听外面一阵吵闹。
“让开,让开,我听说福伯病了,特来看看。”随着话语,外面走进一三十几岁的中年男子,男子白白净净,长得甚是俊朗。
我一见认识,这男子叫洪天赐,他爹是茅山教一名教徒,这洪天赐跟他爹学了一些本事,后来她爹死后,他就四处为人画符驱灾。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他见村民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我和师父,所以看我们很是不顺眼。
洪天赐走进来一见我在场,嘴角一撇,冷哼了一声,然后又看了看福伯,我注意到他看完福伯后,脸色就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