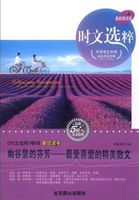2007年9月25日,早晨9点刚过,我们离开额济纳旗的达赖库布镇,踏上重返黑戈壁的旅途。黑戈壁、黑喇嘛、马鬃山、谢别斯廷、明水古城就在前方,使人激情难抑。“胡杨节”前夕,色彩斑斓的额济纳将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是我第四次前往马鬃山。25日的白天和晚上始终满天阴霾,而且行程相当坎坷,原本半天的路途,竟整整走了二十小时。这二十小时,我们穿行在中国西部最大的荒漠,而我沉浸在回忆与思考之中,几乎忘记了与黑戈壁、黑喇嘛无关一切……
我把所了解的有关黑喇嘛的种种,都写进了长篇纪实文学《黑戈壁》。
写完《黑戈壁》,我反而为一种特殊的距离感困扰:通过近四十年探索,我本应成为最熟悉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人,可结束了写作过程,我却觉得黑戈壁更神秘,黑喇嘛更虚幻。是遗漏了什么不该遗漏的细节?是错误理解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不管究竟是为什么,我都希望通过重返黑戈壁,能有所改进。酒泉市电视台为拍摄电视专题片《黑戈壁》,由副台长秦川领队组成了新的考察队,我们一同在十·一前夕,踏上重返黑戈壁的行程。
26日凌晨5点,我们才到达马鬃山镇。在安排住宿的间隙,我走上空旷的街道。
这时,小镇开始苏醒,街头已经有了炊烟与人声。马鬃山镇中心的标志是三只北山羊。望着这伫立在街头的栩栩如生的塑像,我如同一个运动员在起跑线上等候发令枪响,如同一位歌手面对如痴如醉的歌迷等待前奏曲结束。我在等待太阳升起。
“杨教授……”有人从远处赶来,大声招呼。那是马鬃山镇镇长娜仁娜。前几次来马鬃山,她都曾热诚相助。这次来之前,娜仁娜已经调到县上任职,没想到又在镇上相逢。娜仁娜是蒙古族,她名字的含义是“阳光”。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朝霞正好挣脱了浓云的束缚,霞光投射到三只北山羊身上。我知道,我不用守候在街头作第四只北山羊了。从这一刻开始,重返黑戈壁的考察队已经集结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在马鬃山镇的调查,深入而且有成效。马鬃山的居民不但记得我,记得我们的考察,自我离去之后他们用特殊的参与,填补着我们留下的空白。他们已经不只是被调查的对象,成了马鬃山历史的共同撰写者。
第二天,我们踏上前往谢别斯廷泉的路途。
谢别斯廷泉是黑戈壁的北方门户。关于谢别斯廷泉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整整八十年前。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从包头出发,先到达了额济纳。经过休整,于1927年初冬,分几路启程前往新疆哈密。中瑞双方的团长徐炳昶与斯文·赫定率领中心分队,沿黑戈壁北边的古道前行。途中,斯文·赫定得了严重的胆囊炎,而且为风雪酷寒困扰,骆驼已经到了驼载极限,粮食也快用完了。为了不把整个团队拖垮,抵达谢别斯廷泉之后,斯文·赫定决定自己暂时留在泉边,其他人在徐炳昶率领下尽快前往哈密。同时,斯文·赫定将这个荒漠甘泉命名为“那林谢别斯廷布拉克”。“那林”是考察团的瑞典籍地质学家,谢别斯廷的经纬度是他测定的;“谢别斯廷”是本地原有的地名;“布拉克”在西北民族语言中含意是“泉水”。
多年以前,我就有一个夙愿:对西北凡与斯文·赫定等探险发现有关的地方,都要重返故地作追踪报道。谢别斯廷泉正是其中之一。可谢别斯廷今天到底在哪儿?则需要做认真的调查。1990年,在刚出版的《中国地图》上,我发现了一个位于中蒙之间的地名——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它无疑正是“那林谢别斯廷布拉克”的异译。这个发现叫我激动不已。我曾称它为“中国最长的地名”——长达十个字,同时,它也是仅见的包含有外国人名字的地名。此后,我获悉了另外一件与谢别斯廷泉有关的往事。
1962年,为正式划定边界,中国与蒙古国开始谈判。在确认西北边界走向时,蒙古国提供了一幅历史地图,上面标示出清代某时期内外蒙古的界限。如果以它为基础划定边界,那么额济纳(特别是居延海)、黑戈壁,都将有很大一部分位于境外。特别是,酒泉卫星中心将距离边界太近。周恩来总理指示谈判代表:我国将提供另一幅更重要的地图。并要求以这个地图作为确认边界走向的主要参照。这就是由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测绘的《斯文·赫定1927年~1935年中亚考察地图》。最终,蒙古国在得到苏联首肯之后,承认那是国际公认的权威地图,反映的是现代边界走向,两国边界将以其为主要依据。那幅地图标明,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线位于谢别斯廷泉以北。谢别斯廷这荒漠甘泉不但成为探险考察史上的重要地点,还是内陆亚洲地缘政治的从不游移的地标。
2005年,我再次来到黑戈壁,采访时认识了从部队复员的蒙古牧民达布,我问是不是有谁知道、或去过谢别斯廷,他竟然回答:“我当兵的时候,有一年时间,就是在谢别斯廷泉水边上站岗。”在他带领下,我们顺利找到了那个泉水。如同八十年前一样(如同千百年来一样),谢别斯廷泉就掩映在浓密的芦苇丛中,静静地等待我们来临。达布站岗的地点如今成了边界的界桩。
后来,一个瑞典朋友来我家做客。我们曾一同作过环绕塔里木的考察。他听我谈到在黑戈壁的探险,在谢别斯廷泉的寻访,特意问:在谢别斯廷泉还能见到斯文·赫定1927年年底扎下的75号营地吗?我迟疑着,摇摇头。我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谢别斯廷是一个地域的名字。有一股从不干涸的清泉,清泉为大片芦苇掩映,是它的地表特征,所以,它又叫“萨拉赫鲁逊”——黄芦岗。实际上,目前在边界的两边,都有名为“那林谢别斯廷布拉克”的地方。所以,谢别斯廷这个名字,并不能完全与当年斯文·赫定的营地对应。只有那个清泉,才是斯文·赫定的治病秘方,才是古往今来丝路旅人的归宿地。2005年,我见到了泉水汇聚成的池沼,见到了在这里交汇的东西向与南北向的古道。但这并不能使与探险发现有关的生动往事完全落在实处。那个拯救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干渴疲惫的队伍,那个使丝路最大的驼队(有一千二百峰骆驼)得以顺利进出新疆的丰沛泉水,绝不仅仅是一汪四溢的沼泽。驼队的营地,取水的地点,不可能什么遗迹也没有留下。谢别斯廷泉是丝绸之路得以存在依托,是旅人走向的路标,它不应该仅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小的圆圈。
2007年9月27日。我们再次来到谢别斯廷。时过两年多,新修的国门已经落成,边界沉静肃穆,使人驻足四望。
据斯文·赫定的笔记与其他有关文献,在谢别斯廷泉扎下的75号营地位于泉水以南约一百公尺处,比较平整,并且为红柳包环绕,营地边上有个高岗,只要有新的驼队或骑手临近,赫定的助手们总要登上高岗眺望。在一个多月之间,西北科学考察团扎下的两顶帐篷,成了谢别斯廷泉边的风景线。只要确认了当年泉水的地点,就可以推测出营地的位置。
在与国门相对的路边,有一处人们经常取水的地点,可这并非当年的谢别斯廷泉。这个地点无疑是与半个世纪以来的中蒙交往有关。它依道路而存在,道路却是南北向的机动车辆压出来的。沿着水源地的边缘向西、向芦苇最浓密的地方走了几十步,我突然辨认出一条隐约可见的小径探向芦苇纵深处。小径是常年由人、牲畜、动物践踏而成的,没有任何人工修整的迹象。
我与秦川沿小径进入了芦苇纵深处,里面另有一番景象,芦苇高达三四米,如同密集的竹林,小径指向一口古泉眼,泉眼之上,不但覆盖着原木搭就的棚子,居然有一具铁皮制作的人字形棚顶。从形制、材料看,它的制作出自珍惜甘甜泉水的旅人之手,它覆盖的无疑是谢别斯廷泉——丝绸古道的支撑点,丝路行旅的企盼。退出苇丛,向南望去,75号营地只有一个选择,那是由一组红柳包环绕的平滩,与附近草滩相比,几乎寸草不生,显得相当扎眼,显然是因为人在这个面积之内活动所致。视野之内仅有的制高点就在平滩的一侧。望着那离泉水近百米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袅袅升起的炊烟,听到了人声犬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