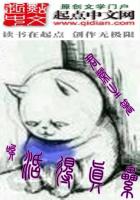承接上章,
政宜只身进入“牡丹纺”,牡丹纺是个大型工纺,牡丹纺里纺织的牡丹的富贵华丽的色彩布都绵长地搭着竹竿晾干。卷卷布弄散开来,从顶垂下,像一匹小小的瀑布从桥洞上垂进水里。铺在地上的布忽的扬起来,像涨水一样,越来越高,越过了政宜的头顶。政宜看着身边这片花布的海洋淹过自己。架在布下的竹竿抬起,随着布匹越扬越高,把所有的布都搭在高高的架子上。纺间里,美丽的花布在月色里顿时高高飘扬。“货带来了?”若干牡丹花布后面隐约见到有个女子正在纺纱,政宜神情缓和了,背负着双手,仰首望往天空,笑道:“带来了,但你们活不长了。“弓弦在拉紧,政宜掀开一层一层花布,隔着最后一层花布,淡淡地对纺纱的女子道:”螳螂一捕蝉,总有只黄雀在后面。你知道吗?“纺纱女子不言语,不纺纱了,梁上传来被勒死的挣扎声。
自从在那晚在洞里救申府三小姐,政宜就判定暗中有两股力量在互相牵制。听到纺纱女子的闷声闷气的声音,曾几何时,政宜在洞里听那”娘子“傀儡也是这般声音。一听这声音,政宜就敢推断,牡丹坊里又有人命要被了结,只会留下这纺纱的女子。政宜昂着头,瞪着眼,用力扯下最后一帘花布,果然又是个傀儡女子!政宜用匕首把傀儡上的线都割断,抱着傀儡就开了门,对无情道:”牡丹纺一会儿就会起火,你把这个傀儡交给申老爷。“说着就把傀儡搭在无情身上。
政宜满脸含笑地看着无情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无情一只手搭了上去,政宜撂开他的手,自己又好气又好笑,道:”我是要你身上的银子。“无情叹了口气,从袖口里取出五两银子。政宜把银子收着,又把手伸了出来,无情哎了一声,政宜是会算账的,自己外围禁军统领的月奉早被政宜算得一清二楚,无情又从怀里拿出二两银子,政宜揣了进去。那支打算盘的纤纤玉手又伸了出来,无情痛苦地望着天含着泪,从领口里取出一两碎银子,自己转了一圈,又把所有口袋都翻出来,道:”大小姐,再没有了。“政宜的手还伸得老高的悬着,无情看着政宜的手,自己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欠了这小女子什么。只得解开腰带里,从里面取出三两银子。无情高政宜一个头,政宜踮起脚,抬起手,下死劲儿用指头点了无情一下:”铁公鸡。“这一指头差点没把无情点晕了。“你去哪?”政宜自然是回赵肥婆的客栈。
政宜用广袖蒙着脸,不顾一切地一路开始狂奔,在夜色的掩护下,筋疲力尽地回到赵肥婆的客栈里,听见走廊里一声惊呼,转过头去,是赵肥婆疯了似地朝政宜挥舞着胳膊,手里拿着笤帚和铜铲。“快进来,丫头。”赵肥婆激动一边说,一边打开掌柜门,“快进来,告诉俺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俺在客栈里是心急如焚,俺打听过路人,说牡丹纺走水了,烧了起来。”政宜早就决定把最危险最曲折的经过守口如瓶,只跟赵肥婆分享最后结局的谎话:“匕首都已不在了,银子拿回来了。”这是赵肥婆希望听到的,也是政宜想告诉她的,故事的其它部分将与赵肥婆无缘。赵肥婆掂着手里的银子,笑道:“楚国男人的小家伙有救了。”
政宜喘了口气道:“我要去楼上见苏先生。”赵肥婆问道:“晦气的很,见他干啥?”政宜又编了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谎话。赵肥婆便自己一径去寻奶妈去了。
政宜敲了门,门开了一线缝隙,蜡烛跳动的温暖光茫,透出来了申貌辨交代的人,甚是衣裳褴褛,却不失威严贵气。政宜挤入屋内,忽地一行大礼,伏在地上,中气十足,道:“季子,受委屈了。”这时的苏秦啃着窝窝头,才低头看清眼前的女子,脸色凝重,道:“你怎知道我的字号?对一个潦倒之人行此大礼?”政宜清了清疲倦的声调,缓缓道:“尊阁现下潦倒,是因紫宸朝中的眉仲瓶为难。眉仲瓶一倒,尊阁恐怕还嫌行此大礼之人之多,多的来口不应心。”那苏秦顶多三十未至,而眼前的十九未至的女子却老练到三十之多。苏秦挨往椅背,笑道:“你又是哪家的说客?“政宜道:”申府,申貌辨。“苏秦打了一个激灵,愕然道:”申中堂?“政宜斩钉截铁道:”正是。“苏秦望往房梁,脸上露出回忆的神情,缓缓道:”你说说连横合纵。“政宜颔首,沉声道:”现今七国乱世,连横为东西向,合纵为南北向,前有惠子于魏连横、后有公孙衍继承,以六国连横抗衡禾国,保持诸国平衡,止息战争而不亡草民性命。“苏秦眼中射出奇光,这女子的像是自己的旧相识。政宜说着,低着头献上一个铜符并锦囊,苏秦接过一看,脸色一变。政宜道:“趁此螽斯之乱,紫宸都城之乱,先生持此符就能逃出紫宸国,若能出紫宸国,再启锦囊。”政宜说完,又行一大礼,直到此刻仍是低着头,不敢望向苏秦,缓缓起身,霍地转身在破桌子上恭敬地放下三两银子,苏秦道:“何名?”她轻轻道:“无名。“
细碎的脚步声响起,政宜出了房门,消失在天色微明、劲风呼呼的紫宸都城中,苏秦掀起遮窗的布帘,往外望去,在窗外看着她的越来越小身影,摇头仰望着即将隐去的紫薇星,长长呼出一口气,叹道:“她身上有仇啊。“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