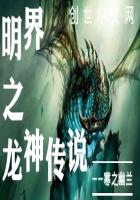我跟方姑姑走出慈安宫,走到罕有人至的小径上时,长风赶了上来。方姑姑是过来人,看出端倪,向长风行礼道:“奴婢先行告退。”
只剩下我们两人了,他情不自禁地上前扶住我的肩膀,急急地问:“半月未见,如何消瘦憔悴成这样?是不是上次病后一直没有调养好?”
说得我眼泪都快落下来了。本来天天苦撑,已经麻木,此时却觉得委屈得不行。好像在外边受人欺负的孩子,在家人面前才会露出软弱。
我在要脸还是要命的问题上纠结着,拿不定主意是否告诉他实情。
见我不语,他略为尴尬地放下手,轻声道:“若溪,我很怀念我们在牢里的那段时光,那时候的我们心意相连,无话不谈。而如今……”他愧疚地自责,“是长风辜负了你。”
天啊!什么叫辜负了我?真不知道古人的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不会是以为我对他相思成疾吧?我是很喜欢他,但是为了一个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真不是本姑娘的作风。再说他压根儿也没对我怎么着啊!既没有勾/搭引/诱,又没有始乱终弃,不能回报我的感情就叫对不起我吗?
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别说得这么别扭,咱俩儿还到不了那层负不负的关系,撑死我就是个单相思。再说我也不是想你想得衣带渐宽,容颜憔悴的。你别跟着瞎掺和,不是自己的责任就不要乱往身上拽。”
长风脸腾地一下红了,呐呐道:“是长风想多了……”
我很悲愤,“是你想少了。”
他不明就里的看着我,茫然的神色非常可爱。我决定了,命比脸重要。能救我的人只有他了,留在凤仪宫还不知道能不能熬到江映容回府那天。想到这里,我撸胳膊挽袖子,义愤填膺,“都是你那个表妹!”
“映雪?”他失神地问,疏忽之下都没有称呼皇后娘娘。
我无语啊,他心里只有那一个人。我都没工夫计较那些了,什么情啊爱啊的,先一边儿放放,小命儿要紧。
“不是皇后娘娘,是江映容那丫头。她一门心思想嫁给你,以为你看上我了,就看我不顺眼,糊弄着皇后说是跟我学茶道,其实是将我要到她身边,天天折腾我。不给我饭吃,不让我睡觉,没事儿就让我跪在地上顶铜盆儿,要不就是举着蜡烛给她当烛台,我上次生病就是在过道里顶盆儿顶出来的,跟她说话不自称‘奴婢’就要挨打,开始还用手打呢,后来大约嫌手疼,要不就是觉得打得不够过瘾,最近都换鸡毛掸子了……”
我卷起袖子给他看我胳膊上一道道青紫的印子,看得他怔怔地发呆,我放下袖子,“别处不方便给你看,你自己发挥想象力吧!……”
我的控诉大会开了足有半个时辰,所有的怨气都倾泻而出。我压根儿就没去想长风会不会怀疑我搬弄是非,夸大其词,会不会不信他那娇滴滴的小表妹是这样一个狠毒龌龊的人。我就是知道他会相信我。
长风听着我的血泪史,面色越来越凝重,抿着嘴,皱着眉。我终于说累了住了嘴,气喘吁吁地看着他。
他别过脸去,不忍再看我,一脸比自己挨打还难受的神色,沉声道:“怪不得我每次去凤仪宫都见不到你,容儿总是说你有事儿不在,我还以为是你不愿见我,故意躲着我。”
“我躲着你干什么?我就跪在隔壁的杂室里呢,你们的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
他胸膛起伏着,一向温和的脸庞也染上怒色,“我去找皇兄皇嫂,要你跟我回府,你等我。”
说完扭头就往凤仪宫走,被我一把拽了回来,“皇后娘娘这几日保胎呢,这事儿不能去麻烦她。皇上那里你更不能去,这宫里的宫婢从理论上来说,都是皇上的女人,哪有跟他直接要的。再者,若让锦夜知道了,我们连退路都没了。”
他停住,想了想,“那我这就去向太皇太后求要你,只是……”他迟疑了一下,羞涩地看了我一眼,“还得委屈你顶着我的侍妾这个名分。”
我都混到这份儿上了,还管以什么名头出去的,只要能离开这里就行。忙不迭地点头,“就当我吃点儿亏,只要一离开皇宫,你就给我一纸休书放我走就成。”
他略不自在,还是点头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