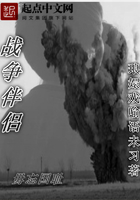白霜鹰怔愣一下,声色俱厉的对黑衣汉子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小爷今天就放你一马。"
"谢谢大爷的不杀之恩…谢谢…"黑衣汉子又像捣蒜似的朝白霜鹰磕头谢罪。
"行了,快滚吧!"白霜鹰不耐这些虚伪做作的过场,从黑衣汉子身边撤回长剑,摆了摆左手,悻然的道:"你好自为之,最好不要让小爷再看见你。"
"谢谢大爷。"黑衣汉子爬起身来,扭头不要老命的朝那片苍林中奔去。
白霜鹰太马虎大意了,他完全没有察觉到黑衣汉子在扭头兔脱的那飞快的一刹,嘴角边露出了极其得意,极度惬怀的诡笑。
假如白霜鹰真的察觉了黑衣汉子的笑容,更洞悉了其中的涵意的话,定然不会轻饶。
斗场中,一具具扭曲怪状,丑陋肮脏,血肉斑斓,支离破碎的残尸是那杂乱无章的,千奇百怪的,恐怖慑人的堆叠着,仆躺着,仰摆着,令人触目惊心,毛发悚然。
晚风徐徐,浓郁的腥气随风飘送,催呕晕血,草木萧瑟,呈现出一派荒凉,肃杀的气氛。
白霜鹰释怀吁了一口气,将长剑上沾染的血渍擦拭干净后,在手里翻转了两下后,"呛"的一声回插入腰间的黑皮剑鞘,动作迅捷而利索,简直酷毙了。
他仰望苍天,兴味索然的叹喟了一声,黯然的摇了摇头,似乎在为自己的碌碌无为,默默无闻而感到无穷的忧郁,无限的惋惜,无尽的怅惘。
是的,白霜鹰年方二十三了,与他同龄的至交好友现已成就为光前裕后的大侠客,而他还是个初出茅庐,懵懂迷惘的无名小辈。由于涉足江湖太晚,对世间的人情冷暖还格格不入。
白霜鹰的命运既是悲惨的,又是侥幸的。其父是威名喧赫的大内五虎将之一,是圣上御赐的金龙密捕,也是邪门歪道闻风丧胆的大煞星——荡魔大侠白云武。可见,白霜鹰是货真价实的将门虎子。
然而,命运注定他要在风雨中,坎坷里成长。他刚刚出世之际,母亲就因恶疾而暴毙,他三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因任侠仗义,广树仇敌而惨遭奸人谋害。就在他痛失双亲,无依无靠的危难关头,命运之神又向他敞开了光明的大门。
他父亲生前的刎颈之交,咤叱剑道的快剑神翁赵天龙古道热肠,义薄云天,毅然收养了故友的遗孤。于是,他就荣幸的成为了一代剑道霸才——快剑神翁赵天龙的唯一谛传弟子,被赵天龙视若己出,掌上明珠,无论走到大江南北,踏遍千山万川,师徒俩总是形影相吊,甚少离分,二十多个寒暑皆是如斯。
白霜鹰在严师慈父的悉心教导和抚育下,苦心修练横空绝世的剑技——快剑三十六招。一学就是二十多个春秋。
直到年初,师父忽然要他出山闯荡江湖,也在这个时候,师父才告诉他父亲白云武是被奸恶歹人所害,责令他务必要报仇雪恨,但仇家仅告诉他了一个西陲霸枭王伦。就这样,白霜鹰含悲洒泪,依依不舍的辞别了相依为命多年,彼此亲若父子的恩师,带着一腔热血,揣着满腹仇怨,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的从遥远的山东奔赴到陕西,誓要手刃他生平所要索讨的第一笔血债,对象是西北黑道巨枭,恶名昭著的双蛇帮之主——西陲霸枭王伦。这是白霜鹰平生首次单独涉入尘世,在师父的身边偎依得太久,也就不谙人情世故,更不善社交辞令了,再加上人地生疏,这些天他就如同瞎猫逮耗子似的在三八里秦川东飘西荡,盘缠都快花光了,仇家的一丝一毫的线索都没有打探到。
失望之余,他忽然想起了四年前随挚友造访华山时,结识到的华山掌门人——大名鼎鼎的君子剑张照光,当即就欣喜若狂的奔赴华山,试图从张照光那里打探一些有关仇家王伦的蛛丝马迹,殊不知,华山派竟然莫名其妙的被官府指为叛党而重兵剿除,张照光却又神秘失踪。
他怀抱着恩师当年技压群雄,叱咤风云的斩虎剑,形只影单的在阴翳的林子里奔驰着。剑本来是寒森森的,冷冰冰的,但在他的心目中却是暖洋洋的,热烘烘的。
是的,一箫一剑平生意,像他这样的傲啸江湖,快意恩仇的刀客剑侠往往都是单枪匹马的,那份孤独,落寞,寂寥的感觉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浓厚,然而只要有兵器相随他的心就不会寒冷,就不会凄凉。
苍林里是雾沉沉的,阴气森森的,黑咕隆咚的,林木纵横,枝蔓叶茂,能见度极为有限。他依恃着超强的目力,健步如云飞似的朝适才铁胆包天马中周逸去的方向疾驰,他必须要找到马中周,迫切的想要从他的口中追查到一些有关双蛇帮和仇人王伦的线索来。
突地……
"当""当"两声清脆的金铁敲响在空气中掣出一串悠忽的颤音,紧接着就是"哇呀"的一声凄厉惨嗥连同那两声金铁敲响硬生生的撕破了苍林的幽寂,剐碎了林子间死气沉沉的氤氲。
白霜鹰怦然心惊,听声辨位,这声惨嗥传自于二十丈以外,对于他这等武学高手来说是近在咫尺的距离。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白霜鹰将斩虎剑往腰带上一插,搓了搓手,一股豪气直冲云天,双脚就地轻轻一蹬,纤瘦的身形疾弹而起,像煞一只精灵古怪的猕猴,那么迅捷的,轻巧的,灵敏的在犬牙交错的林木间跳跃,径直的朝二丈以外掠去。
兔起鹘落之间,白霜鹰就掠过四十多棵参天大树,一股浓郁的,略带铜臭的腥味夺鼻而扑,熏得白霜鹰心里微微作呕。
他当即滞住身形,目光如电的朝四下的一草一木搜视过去,天啦,距他停身之处不到三米远的一株矮树的枝桠上悬挂着两条血流血滴的大腿,其中一条腿的胯部赫然扎着一条白手绢。矮树下面摊堆着一大截没有头颅的躯干,森白的颈椎骨戳出体外,五花八门的肠脏筋筋绊绊的,血淋淋的扯得满地都是,嫩红而瘰疬的黏糊肉糜溅贴在四下的树杆,枝叶上,狞怖得就像是一块块刚刚切削好的生鱼片似的。
几声冤鬼悲泣的夜鸟啼叫悠荡的传进白霜鹰的耳鼓里,他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颤,顿觉浑身鼓起鸡皮疙瘩,头皮倏然炸裂开来。
土黄色的布屑鹅毛般的在夜风中飘荡。
顺着地面上的一串腥赤的血印搜视过去,在一大蓬杂草野花中间滚落着一颗突目切齿的人头,汗渍和血浆将乱糟糟的长发凝结在灰败的,五官扭曲的面孔上,再加上一脸的污垢,疤痕,恐怕是天王老子也一时难以辨别出死者是何许人也? 白霜鹰电般掠到那颗头颅跟前,俯身仔细一辩认,不由得再次大惊失色,直惊得打了一个倒退,这是一张方形的脸,高高的鼻梁上方一双死灰色的老虎眼珠暴瞪得就欲凸出眼眶,黯淡得毫无光泽,但充斥着难言的怨毒和仇愤,是一种凄苦,也是一种无告。
这张脸,这双眼,白霜鹰是再熟悉莫过了,这死者竟是刚刚从虎口下脱生不出一个时辰的铁胆包天马中周。原本以为他可以逃出生天,却不料再次掉进狼穴,而这一次是神仙也无能为力了,他被人歹毒的劈成三块。
白霜鹰倒抽一口凉气,额头上隐隐的渗出汗液,一种仇毒无形的在全身的血液里侵蚀着。论身手,马中周当之无愧的可以列为武林中的二等高手,据适才那两声短暂,干脆的金铁交击声来看,他在突遭敌袭交手时,应该是在两招之内被凶狠恶毒的敌人肢解成三块。像他这等登堂入室的高手竟然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生死活裂,足见这人的身手之高已达难以估摸的境地,至少也是顶级的剑道高手。
白霜鹰悲愤填膺的挫了挫牙,心忖:这人出手如此残忍,狠毒,酷虐,很像传言中的那些凶残寡绝,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的江湖杀手,很显然虐杀马中周的凶手不是官兵,而是另有其人,那这人会是谁呢?杀人的动机又何在?
白霜鹰僵直的立在马中周的残尸旁,带着无比浓烈的怜悯和怅恨,凝神寻思着。
"哈…哈…哈…"
一长串悲凄幽婉的笑声穿云裂雾的响彻在森然,僵寂的林子里,笑声宛若夜枭悲泣,冤鬼哀号,端的令人毛发悚然,心悸神摇。
白霜鹰急敛心神,警惕的按上了腰间的剑柄,面颊上的肌肉紧绷,瞳孔在剧烈的伸缩,电炬的目芒飞速的扫向四西八方。
目光触及之处,除了黑压压的,密植得像乱发一般的林木树枝外连半个鬼影也没有,就仿佛那串愕怖的笑声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不是从活人的嘴巴里迸发出来的。
白霜鹰抹了一把冷汗,那串听来勾魂摄魄的恐怖笑声又隐挟在僵硬,冷瑟,压抑,紧张空气中飘进了他的耳鼓。
他强压惊魂,豪勇无畏的劲头由然而生,撕大嗓门,声若洪钟大吕的喝道:"何方高人,既然雅兴来造访我白某人,为何要靠躲躲藏藏,装神弄鬼来混淆视听,不怕惹得天下人耻笑?"
"休得大言不惭,恶语中伤。"一声穿云裂石的叱喝霍地的传自白霜鹰的身后。
白霜鹰大吃一惊,电掣转身,立见身寻丈外的一棵巨树下卓立着一个体魄魁伟,披着一件油亮黑皮大衣的蒙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