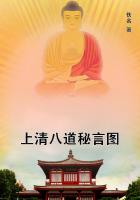胖子来到了塔下,那张因为年代久远而发黄的纸,在手心被用力攒成了一把扇子。
他徘徊着,握着纸的拳头,不停地击打另一只手的掌心,油光发亮的额头,硬是被挤出了一个川字。
如今的街道变得格外冷清。
也许很多年后,市场口的猪肉荣,会大声地对着自己不怀好意地开玩笑“胖子,新鲜猪腰子,来一付,保你虎虎生威,威猛无比。”或者,市场深处米铺的小刘,还会拉着自己的俏媳妇,对自己行个礼,开心地笑着问候道“大掌柜,您儿今天真早。”只是啊,那个熟悉的豆腐摊,再也不会出现了。老王早就被鱼头怪戳烂,而他老婆,也刚刚死在怪物破城的那个白天。
不知道以后是熟悉,还是陌生,或者一切都不存在,包括自己。
胖子叩开了塔门,来到了塔顶,伸出手,递出了那张皱皱巴巴的纸,然后立在一旁,恭敬地看着面前的女子。
这个塔顶,对他来说非常的陌生,上一次来,还是儿时病到瘦骨嶙峋无法医治的时候,不知父亲花了怎样的代价,把自己带到这个地方,朦胧中,就是眼前这个明黄衣服的女子,治好了自己,虽然落得了这样一个身材,但也是常年无病。
可是这个塔顶,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又是十分地熟悉。一张檀木桌,一把梨木椅,还有窗边的身着明黄衣服的女子,所有的一切,都和那时一模一样。
明黄衣服的女子,一直没有老去。
这是整个城堡的人们心知肚明却从没在脸上表露出来的公开秘密。
见明黄衣服的女子没有任何的回应,胖子默不作声地退了出来。出来后,胖子犹豫了一阵,然后他来到了城东的城墙上。
这几天,城头出奇地安静,因为鱼头怪们比较安静。
他们倚靠在沙地旁的树干上坐着,有的懒懒散散地晒着太阳,有的看着从叶缝中洒落在身上的光斑发呆,还有的,两两一起嬉戏着。而在树林的不深处,有一个鱼头怪,甚至用自己尖利的指甲,在树干上刻着什么。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离这个鱼头怪够近,他会惊奇地发现,树干上刻画的是一个‘秦’字。
在这个鱼头怪刻画第二个字的时候,树林里窸窸窣窣传来一阵落叶的响声。
原来是鱼头怪们纷纷站立了起来。
只见从林子深处,一个男子背着长剑缓缓踱步而来,衣诀飘飘,青丝飞舞,发髻上的纶带长长地垂到了腰际,修长的双臂反背在后,犹如仙人下凡,似神灵印世。
鱼头怪们都毕恭毕敬地低头在侧,不敢有一丝声响。
男子看着这些鱼头怪们,仁慈地眼中有着复杂的情绪。
我们都是痛苦的。他喃喃自语道。
鱼头怪们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唧唧叫着,显得异常兴奋,然后朝着那座围而不困的城堡
冲去。
这不是之前惩戒式的冲,也是猫斗老鼠般的冲。
这次的冲锋,带着毁灭的气息,席卷着林地的落叶和沙地的尘土,朝着那座城堡而去。
看着席卷而来的漫天尘沙,城头的人们惊讶了!数息的寂静之后,尖叫声,哭喊声,兵器之间的磕磕绊绊声,终于平衡了尘沙里面的怪嚷。
鱼头怪们很快爬上了城头,逢人挥爪,中者应声而倒,即刻摔为两截,还在抽搐的身体流出满地的血肠。
那个先前蜷缩在墙垛呕吐的青年,再也承受不住,拿起手中的已经卷口的菜刀,朝着自己的脖子抹去。
菜刀不够锋利,只是将脖子割出了一个口子,喷涌的鲜血撒在脚下同伴的身体上,青年哀嚎着捂住伤口,爬上墙头,朝着护城河坠去。
如今的护城河,已经失去了护城的作用。河里密密麻麻堆满了人们和鱼头怪,还有插在他们身体里未来得及抽出的兵器。
青年就这样掉落在一只长矛上,长矛穿过他的胸口,汩汩的鲜血顺着长矛挣脱着身体的束缚,欢快地四处流动。
兵人奋力地挥动着手中的刀。
刀上镶着一颗美丽的蓝宝石,这是他从故国带过来的。
二十年前的时候,他亲眼看着一个男人拿着这把刀砍鱼头怪;十二年前,他也手握这把刀砍过鱼头怪。如今他还是拿着这把刀砍鱼头怪。
这一刻,他感觉他这一生有砍不完的鱼头怪,他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鱼头怪,他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国家,失去了战友。
也是因为鱼头怪,他所奢求的幸福生活也被打破了。
他满是血迹的脸上,露出悲哀的笑容。
他放下了手中的刀,不再打算抵抗。
他想回头看看生活了12年的城堡,却看见了一个身影,那个曾经把花瓣泼他一身的女子,如今的妻子。
女子跌跌撞撞连走带跑,手里似乎抱着什么包裹。
兵人心中羞愧难当,眼眶一热,拿起刀逼退几个鱼头怪,跳下城头,直奔自己的妻子而去。
刚想责备她几句,只见女人摊开双臂,露出了她怀抱的东西。
兵人噗通一声跪在面前,丢下宝刀,仰天捂脸嚎啕大哭。
女人默不作声地揭开包裹,露出里面的金色战甲,披到自己夫君的肩上,细心地系上藤带,然后扶起眼前的男人,将一方玉玺塞入他的衣带,轻轻地道,
“似一国之君那样去战吧,君在,国便在;国在,家便在;家在,奴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