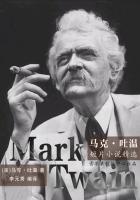我现在真像上面所讲的一个人毫无牵挂地在世界里,年纪还是青青,容貌仍然很标致,人们都这样说,请你相信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袋里也有相当的财产,我的确是自视很高。有好几个大商人向我求婚,有一个是特别热烈的。一个布商,我丈夫死后我就租居在他家里,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在他家里我有一切的自由同机会可以恣意享乐,与我所喜欢的人们一块消遣,我居停的妹妹是世上一个最胡闹、最爱享乐的女人,她的道德观念并没有我起先所猜想的那样好。她带我到放荡人们的世界里去,甚至于带回家几个她很喜欢的人,特别来看她的漂亮的寡妇,她总爱这样叫我,不久大家都用这个绰号了。我的声誉既然是这么大,再加上这班傻子,我在那里真是格外地受他们的见爱,有一大群人捧我,还有许多男子自命为爱人,但是在这许多男人里我却找不出一个惬意的求婚人。至于他们通常所用的诡计,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不会再陷到那种阱里。这回我的情形是与前不同了,我自己袋里有钱,用不着向他们要什么东西。我曾经有一回给那个大谎——所谓爱情——骗过,但是这个把戏却已经收场了,我心里决定这次一定要正式结婚或者就同那人什么关系也不发生,嫁也要嫁得上算的,或者干脆不嫁人。
我真爱同他们在一起,他们都是嘻嘻哈哈,诙谐百出的人们,有的殷勤侍奉,有的气概堂堂,我常觉得他们有趣味,像我觉得别一种人物有趣味一样,但是由仔细的观察我看出最漂亮的人们所干的是最不漂亮的事情——那是说从我的目的方面着想,他们可说最不漂亮的。而那班带着最漂亮的条件来向我求婚的人们却又是天下里最不漂亮,最讨厌的人物。我对于商人并没有什么嫌恶,可是我所嫁的商人必定要带些绅士的风度才行,当我丈夫想带我到宫廷里或者到戏院去,他佩起剑来会很称身样子,走出来也是个绅士,同别位绅士没有多大不同,并不像那种在礼服上面留有围身裙的痕迹,或者假发现出帽子的压痕,不是那种走到人前当人们给他佩剑时候,好像剑是硬插在他身上,满脸露出他那一行的商人的神气。
最后我找出这个两栖动物,这个水陆两宜的东西,所谓绅士式的商人,这真是我的虚荣心的现世报,我真可说是设阱自陷。我说设阱自陷,因为不是落到别的圈套里面,却是我自己陷害了自己。
这个人也是一个布商,因为虽然我的女伴想撮合我同她的哥哥,但是当正式谈判的时候,好像他是要我做他的外妇,不是做他的夫人,我始终是忠于我的一个主张,一个女子绝不要给人养做外妇,当她还有钱自养时候。所以我的骄傲,不是我的节操。我的钱,不是我的道德使我做一个规矩的女人。可是就我的结果看起来,我觉得还是起先让我的女伴将我卖给她的哥哥好,总比现在这样我自己卖给一个商人,这商人同时是个浪子,是个绅士,是个开铺子人,又是个乞丐,强得多了。
但是我却慌慌张张地去干,(心里给“绅士”这个字迷住)把自己毁了,世界上女人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下流地毁了自己;我的新丈夫忽然间得到这一宗大款,就拼命地挥霍,我所有的同他所有的钱,若使他可说有值得一提的钱,还不够维持上一年。
他很爱我有三个月光景,我所得到的是我看他花了许多我的钱在我身上,可说我自己也尝到一些花钱的快乐。“来,我亲爱的,”他一天对我说,“我们去乡下住一礼拜散散心好吗?”“好,我亲爱的,”我说,“我们到哪儿去呢?”“我是随便去那里都可以的,”他说,“但是我想在那一星期内我们要扮成像个贵族样子。我们到牛津去吧。”“什么,”我说,“我们当真去吗?我是不会骑马的女子,坐马车去路又太远了。”“太远了!”他说,“坐着六匹马的马车,没有个地方会是太远了。若使我带你出去,你要像公爵夫人的样子旅行着,哈哈。”我说:“我亲爱的,这真是恶作剧;可是若使你想干,我是不在乎的。”好,定了一个日子,我们雇一辆华贵的马车,六匹壮伟疾驰的好马,一个车夫,一个左侧乘马的驭者,两个穿着顶讲究的制服的仆人;一个骑在马背的跟班,还有一个帽上插着鸟羽,骑在另一匹马上的侍童。仆人们都叫他做爵爷,旅馆的掌柜自然也是这样称呼,我却是一位伯爵夫人了,这样子我们旅行到牛津去,的确逛得很高兴,说一句公平话,世上没有一个乞丐会比我的丈夫更知道怎样摆出爵爷架子。我们瞻览了牛津所有的古迹珍物,同两三位特别学员谈天,说有一个侄子现在是归爵爷照拂的,想把他送到牛津大学来念书,打算请他们做他的私下教师。我们还给几个穷学生开点玩笑,答应将来起码叫他们当爵爷家里的牧师,使他们戴上大教士的肩巾;在牛津住了几天,在花费方面真是像个贵族,我们又到诺坦普吞Northampton去逛,总之遨游了十二天回转家来,一共差不多用了九十四镑。
花花公子总是很虚荣的。我丈夫有这个好处,他用钱素来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他的生平实在没有多少重要的事,用不着详细叙述;所以我只说差不多过了两年零一季光景他破产了,又没有别的财路可通,被抓到执行吏家里去,他的案子太大,不能够保释出来,他就派人通个信叫我去看他。
这事不会使我惊讶,因为我早已看出形势有点不妙了,想法自己尽量留些款子。虽然并不多。但是当他找我去时候,他的行为是出乎我意料地好,他坦白地告诉我,他做了傻子,把自己弄破产了,这本来是可以预防得到的;现在他看来是免不了破产的,所以他要我回去,把家里东西搬走,以后若使我能够从他店里拿走一二百磅的货,我也要干去;“可是,”他说,“你什么也不用告诉我,拿了什么同拿到什么地方去。至于我自己,我决定想法逃出这个屋子,远走高飞去了;若使你再也没有听到我的消息,我亲爱的,”他说,“我总是希望你能够很快乐地过活:我觉得很对不住你,我实在害你不浅。”当离别时候,他对我讲有几句非常漂亮的话;我不是告诉你过他是个绅士,在这点上我所占的唯一便宜是听了许多好听的话;他待我着实不差,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很有礼貌的,甚至于最后一次的会面。不过他把我所有的钱全花完,让我去抢夺债主们应当得的钱,做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就照着他所说的办去,这是你们可以想得到的;这样同他握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在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晚上想法从执行吏家里逃出,亡命到法国去,那班债主们也只好大家拼命争吵一场算了。他怎的脱身我是不知道的,我晓得的只是在早上三点钟左右他跑回家,将我剩下的东西全搬去卖,店也关了,带着他所能够筹到的钱跑到法国去,从那里他寄有一两封信给我,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当他回家时候我没有看到他,因为他既然像前面所说的教我怎样办去,我又用了最快的速度把事办好,我是犯不着再回转家来的,恐怕在家门口会给那班债主逮住;因为破产的揭示快要发出来了,他们可以根据着委员们的命令抓我。但是我的丈夫很敏捷地逃出执行吏的家里,从差不多屋上最高那一层拼命一跳落到别个屋子的屋顶,这座屋子也有二层多高,真是很可以把他的颈项跌断,他却能够安安稳稳地再跳下,跑回家去,将他的东西拿走,他的债主还不能够来抓他;因为他们还没有取到命令,可以叫警官来看管东西。
我的丈夫待我实在客气得很,我现在还要说他很带有绅士们的好处,他从法国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告诉我他在那家当铺里把二十块很好的荷兰布料子只当了三十镑,那东西实在值得九十镑以上,他把凭据寄来,同一张付款取物的亲笔信,我把这项布赎出,前后一共卖了一百多镑,花些空时间把它割断,慢慢地等着机会零卖给住家人们。
但是这笔款同我从前自己暗地里留下的合算起来,我觉得我的情形大大改变,我的财产比以前差得多了;将这些荷兰布,一包从前带走的棉纱布,几套杯盘同其他别的东西一起估起,我看几乎还不能凑成五百镑;我的情形又是古怪得很,因为我虽然没有儿女(我同我这位绅士式布商养了一个小孩,可是已经埋了),可是我是一个有夫的寡妇;我有一个丈夫,我又是个没有丈夫的女人,我不好再去嫁人,虽然我很晓得我丈夫绝不会再回英国,就说他活到五十岁。所以我是限制住了不能够结婚,不管人们向我提出多么好的条件,在这种境遇之下,我又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朋友,最少是没有一个我可以信得过敢把我这种秘密的身世告诉给她的朋友,因为若使法庭里委员得到风声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要被他们传去,先发誓然后再受审,我所救出来的钱都要被他们拿去了。
有了这些恐惧,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真姓名隐埋起来,用一个别的名字。这个我办得很周到,我到一个很偏僻的所在租间房子,穿上孀妇的衣服,把自己叫做法兰德斯夫人。
我就隐匿在这里,虽然我的新认的人们全不知道我的来历,可是不久我天天有很多人同我在一块,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那地方所居的那类人们里面女人的数目太少了,或者还是因为那地方的人们太穷困了,所以比别处的人们更需要安慰些,我很快看出一个可喜的女人是这班痛苦的儿子所非常看重的,那班把欠的债打个折扣还不能还清,天天吃饭要靠着招牌上画个《牡牛》的饭馆挂账的穷鬼们却找出钱来请客,若使他们喜欢了一个女人。
不管我怎样保护自己,像罗彻斯特勋爵的外妇爱她的友伴,却不让他们再进一步一样,我渐渐得到荡妇的恶名,却没有享受荡妇的快乐,为了这个缘故,一面厌倦那个地方,一面真是也厌倦那班人,我开始有迁居的意思。
这真是一个会使我生出奇怪感想的好题目,看到浸在穷苦烦恼的境遇里的人们,他们是连破产的资格都够不上,他们的家庭是他们自己恐怖的对象与别人慈善事业的对象,但是只要还剩下有一便士,不,甚至于不到一便士,他们总是努力用他们的罪恶来浇洗他们的悲哀,重新加上一层新罪恶,极力想忘记以前种种的事情,现在正是他们要牢牢地记着的时候,积下更多的恶行做将来追悔的材料,继续作恶下去,用此来做补救过去的罪恶的法子。可是我是个不善于敷说劝善话的人。这班人的确是太坏了,甚至于我也看不惯。他们的作恶带有怪诞可怕的色彩,因为那种作恶就是对于他们也是很勉强的,他们不单是背着良心,简直是背了天性干事,他们任情胡闹,为的是要淹没他们的可怕回想,这是他们的境遇常常会引起的,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悲叹怎的阻咽了他们的歌唱,他们眉宇间总是毫无血色,带着哀痛的神情,不管他们怎样强颜装欢,不,有时他们会亲口说出他们的不该,当他们刚在为了淫荡的享乐或者放肆的拥抱花了钱之后。我听过他们掉转头来,深深地长叹一声,哀号说:“我真是一个狗!伯替,我亲爱的,我还是要举杯祝你健康。”指他的妻子,她或者连两三个先令都没有,身边又有三四个孩子。第二早他们又要痛悔前非,或者那个可怜垂泪的妻子走到面前,不是对他说他的债主怎样用蛮,将她同小孩子赶出门去,就是别个可怕的消息!因此更加了他的自责,他想了又想,弄得简直快疯狂了,心里头既没有什么稳固的道德观念可以扶持着他,又不能相信上帝,从宗教上得到安慰!只觉得四面全是黑暗,他又跑去用那解忧的方法,那是用酒浇下去,用放纵的行为盖过去,和那班同处在一样环境的人们重演他的罪恶行为,这样子他一天一天向着毁灭的道上进行。
我还没有坏到同这班堕落的人们能够相处得来。却是很严肃地考虑应当怎么办才好,想一想我目下的境遇如何同我应该走的是哪一条路。我知道我是没有朋友的,不,在世上连一个朋友或者亲戚也找不出,所留下的一些款子明显地天天耗费去了,当用光时候,我看是免不了饥寒穷困的。这么一想,对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同天天排在眼前的穷人生活我觉得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决定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我认得一个很端庄的好女人,她同我一样也是寡妇,不过境遇却比我丰裕。她丈夫是一只商船的船主,当由西印度群岛航驶回国的时候,不幸中途遇险,若使他能够安全地航行到家,很可以发一笔财,可是现在却损失不少,他虽然救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忧患之余,他的心可说是碎了,后来不久就死去,他的孀妇给债主追得太紧,只好躲在这块穷僻的所在。她靠着朋友们的帮助很快就把债务理清,又是个自由的人了,她看我也不过是躲避在那里,并不是同什么大案子有牵连,又看出我和她很同情,或者不如说她和我很同情,两人对于这个地方同住民都具有应有的厌恶,她请我到她家里住去,等到我能够在世上找到一称意的安身所在;又告诉我,十分有九分或者有一两个好船主会喜欢我,向我求婚,在她所住的那部分的城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