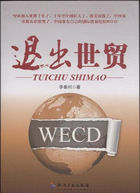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西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犷不要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消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而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心不安。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样,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咸丰五年(1855年)春,是曾国藩十分艰难的日子,湘军在九江、湖口大败,太平军又重新控制了湖北大片地区。太平天国的西征反攻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湘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东征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时,郭嵩焘从湖南专程来到江西,他是在湘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前来安慰曾国藩的。曾国藩看见郭嵩焘的到来,心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慰藉。
郭嵩焘的到来,还让长期跟随在曾国藩身边的刘蓉感到很兴奋。他已经在曾国藩的幕府呆了一年多的时间,非常想辞去这份差使回湘乡老家,可曾国藩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来劝阻。到了南昌之后,刘蓉又提起自己回家的事情,曾国藩便对他说:“什么时候郭嵩焘到了我的身边,就可以考虑放你走。”
现在郭嵩焘来了,刘蓉便旧话重提。曾国藩还是不愿意放行,就对刘蓉说:“我想继续留君于此,可苦于难以措辞,拟作一诗相挽,怎么样?”
刘蓉笑着说:“如果诗真的很好的话,我就答应留下来。”
“你归心似箭,我做的诗再好,你也说它不好,怎么个评判法呢?”“这好办,只要你的诗能将我逗乐,便是好诗。”
曾国藩吟哦片刻,提笔写下一诗,取名叫《会合篇》。
刘蓉拿过来仔细读起来,但见满纸谐句趣语,可细细品之,却又造句奇拙,神与古会,直登韩愈之堂而入其奥,读之可想见轻裘绶带、雅歌投壶的气度。刘蓉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在一旁看热闹的郭嵩焘说着,也接过去读了起来。刘蓉说:“好吧,我先答应再留几个月。这里,我也和诗一首,你们看看怎么样。”他在诗中写道:
滔滔江汉流,频年斗蛇豕。曾公吾党雄,奋起双髯紫。传檄走江南,剑戟森腕底。建瓴方东下,便可楼船拟。空峨诸葛中,谁纳圯下履。仰天一大笑,万事东流水。
曾国藩常称刘蓉是诸葛孔明,刘蓉自己也认为有几分诸葛孔明的才气。有他相助,曾国藩自觉底气增加了许多。
历史上大多有所作为的人,还都是那些富有学识智慧的人。而有学识的人,大多又都较有文采。而文采对于成功者的作用却是不尽相同,但有作用是无疑的。因此一个没有文采和学识的人而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即使有,也仅仅能算是个特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即衡州西北蒸水之滨的衡阳县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二年(1852年),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打听到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有功而不受奖赏。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却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乃温言相劝,多方激励,终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杨载福,亦名杨岳斌(投军后因避咸丰之名载淳讳而改),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战功,父为游击官衔。居湘江滨,水性极佳。早年入行伍,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把杨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入水师,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练习水战。至1854年2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二年(1852年)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实不为过。
如果说曾国藩是靠人气立下绝世之功恐怕不会有异议的。曾国藩礼让人才、强织关系的做法也成为做大事者应该共同遵守的领导法则。
3.与普通大众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
越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与广大的普通大众越要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就叫赢得人心。
对于人民,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儿,就是把人民比成了水。还有,“得民心则昌,失民心则衰。”中国古代,成大事者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能达到此种境界,真是不容易。
只要能得到人心,就能建筑起无数钢铁长城。作为一代英豪的朱元璋,同样也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是宝,因此,他是如此地重视民心,每到一处地方,便收买一处的民心,朱元璋的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为了谋求新的发展,朱元璋率军进兵江南,以图有新的发展。采石城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南岸城池,该城一破,红巾军千军万马顿时如潮水一般涌向城中的各个角落。对于久困和州,粮食供应紧缺、吃过伙食供应不足的苦头的将士来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些牲畜、粮食,在他们心目中是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尽管军纪严明,但出于囤粮为公的心理,都想把东西抢到自己的部队里去。因而采石城破之后,各路将士争先恐后,不管是仓里的还是囤里的,是官家的还是平民百姓的,也无论是衣是粮,鸡鸭猪狗,你抢我夺,抢到手就往船上装载,弄得满城鸡飞狗跳,乱作一团。此时军纪已难以制众,将士们全抢红了眼,此时就是杀几个人也难以遏止。将士们心同此理:饿苦了,饿怕了,因而就是拼命也要饱掠一番,以便能吃上一段时间的好饭。
对此,朱元璋很担心,士兵们都是只图这些眼前利益。他是个很重军纪的人,他为自己军中的一些未直接管辖的部队犯忌而生气,于是抓紧派人组成了纠缉队在街头巡逻,城中秩序才渐归平静。他朗声向部队解释说:“我们这支队伍要成大事,不图眼前的这点儿小利。前面就是太平城,那才是个富庶的去处,兄弟们到那里去,一起去大开眼界吧!”经过这一鼓动,将士们的抱怨才算消退了。接着便是犒赏军队,好猪好牛好米饭,饱餐一顿。
经过这一风波,朱元璋担心在太平城中再起波澜,便在从采石城出发以前命掌书记李善长紧急起草了《戒缉军士榜》,意在约束军队,防止扰民。果然,在太平城,战斗刚一结束,士兵们刚准备动手抢掠、大发横财的时候,却见城中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榜文,上面赫然写道:敢有抢掠财物、杀害百姓者,杀无赦。
朱元璋就是这样重视自己的队伍在民众眼中的形象,他所起草的榜文,很有作用。朱元璋杀一儆百,所以混乱的局面立刻变得井然有序,这样反而保护了战斗力。在战事结束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军士们都有一份。朱元璋的高明做法,既得到了民心,也稳住了军心。
朱元璋在得民心后,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他又在巩固扩大江南根据地的同时,再让自己的新政深入人心。他在占据应天后,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让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对自己的每一步路子都有清醒的认识,他深懂民心。只要有人,就算是“地狭人少”,他依然重视。他训诫说:“我自起兵以来,从未随意杀掠。今尔等带兵出征,望能体察我的心意,严格约束士卒。城破之日,不得妄行杀掠。有违军令者,军法处治。倘再纵容,定当严惩不贷!”诸将战战兢兢,奉命而去,很快就攻下镇江。入城后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种情况迅速传到其他地方,各地士民都称颂朱元璋的军队是仁义之师,这给朱元璋经营江南带来很大便利。攻占镇江后,徐达又分兵占领了金坛、丹阳等县,面向张士诚占领区构筑了一道防线。
朱元璋知道得民心可以安定局面,利用民心可以增强自己的后备储力,是自己威力无形的延伸。对边界问题,朱元璋要求“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在攻克江浦时,朱元璋树起“奉天都、统中华”的金牌,他亲自出征,以便更能激发起人们心中的斗志。而此时敌军人心本已浮动,见救援无望,有些军官便联合起来,开门投降。朱元璋顺利进入婺州,在那里设立军政机构。接着,又分兵四出,占领了婺州周围地区。朱元璋还派人到庆元路(今浙江宁波),招降控制浙江沿海地区的割据首领方国珍。方国珍见朱元璋势力强盛,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又想藉为声援,便遣使进献礼物,表示归附。到龙凤五年(1359年)下半年,衢州、处州等地也落入朱元璋手里,元军在浙东的据点都被拔掉。朱元璋经略东南的战略决策,获得圆满成功。
朱元璋乐于采纳建议,为了倡仁义,收人心,他在根据地的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赢得民心的措施。首先,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义首先体现在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宽减税役。龙凤二年(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复言其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到了龙凤四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县,询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征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这一年,对朱元璋这一规定,当时也有官员想不通,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无以为治。”朱元璋的回答则是:“自兵乱以来,百姓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在经济上,朱元璋设法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龙凤三年(1357年),他亲征婺州时路经徽州,曾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二人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立即下令邓愈停工。唐仲实说话间又婉转地反映“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的情况,意即百姓负担过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做出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显示了愧意。到了龙凤四年,他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1363年)又在徽州落实“民自实田”之策,并要求防止官吏横敛百姓。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过去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当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绩,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徭役,废除新归附地区的旧政,对新归附区的所有税赋和徭役实施“尽行蠲免三年”的政策。
做到此,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于是进行了免租和赈灾活动。他“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他还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朱元璋没有忽视人民,而且懂得爱民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对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公孙丑下》中有这么一段论民心的话值得后来者深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