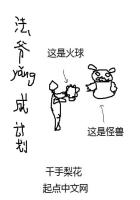她听到呼吸声,两个人,一个沉重一个轻缓,显然是一男一女。窗户上都加了好几层,月光不能照进来,屋里很黑,她吸收花莲的力量,重生后视觉也深度觉醒,眼睛像猫那样能夜视。
她不喜欢暗杀,便轻轻敲了敲门,那两人睡的很死,惊不动他们。她有种做贼的感觉,心里很虚,便又踢倒一个凳子,可这动静还不如敲门。她想起灵犀铃来,撸起袖子使劲的摇,这威力非同小可,里边闹起躁动和谩骂,很快又亮起灯。她也点燃外间的灯,坐下来静等,心里莫名的平静下来,她觉得自己成了神,被赐予生杀大权。
一个中年男子,只裹了件袍子出来,手里擎着灯,两眼迷蒙着,睁不开的样子,脸上的肉像洗过的麻布那样发皱,一见外屋里突然多了个黑衣人,惊的就像吃了冰块,低声喝问一声“谁”,彻底醒了。
红狐背对着她的猎物,她不太会变声,索性就用自己的声音道:“死神。”
那人好似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胡子几乎都直立起来,全身都僵住,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便把蜡烛滴在手背上,将自己痛醒,他必须保持清醒,尽管这一切是如此的突然而荒谬。他也是位绝顶高手,即便面对死神,只要能拼死抵抗就还有一线生机。况且他也是死神,死神不能杀死神,只要戴上面具便就能保住性命。
“你自杀吧,把你的面具给我。”红狐突然感到疲倦,她已很久没闻到血腥,她怕自己会呕吐。
他已恢复镇定,死死盯着那漆黑的背影:“你来错地方了吧,如果你现在就走我只当你没来过。”
“你还是先穿好衣服吧,我可以等。”红狐给自己号脉,她的脉搏轻而急,面具戴在脸上有点重,她扶了扶面具。
“你到底是谁?”他开始仔细观察屋内的一切,在盘算着一旦打起来哪些东西可用,或者可以从哪里逃走。
“我是死神,今夜来取你性命,我劝你最好还是接受审判,你该死。”
“哼,笑话,这世上就没有什么该不该的道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你若真要杀我不防就试试!”他已算计好了一切,只要她起身他就把袍子扔过去,然后以最快速度贴上去用拳头打她的头,他对自己的拳头和速度都很有信心,只要能一拳击中就有了七分胜算。
红狐想大睡一觉,想速战速决,站起身,刚想转身那袍子就像猛虎般扑了过来,她不想被罩住,更不想挨拳头,伸手控制住袍子,把它转成一面盾。
他一口气打出七八拳,全打在袍子上,却像打在水面上,都被弹回来。偷袭失算,他赶紧钻进里屋去,在转身时他感到身边刮过一阵冷风,等进到里屋他第一眼就看见那张面具,冰冷的雪白色,两道清晰的泪痕,在烛光中透着诡异的气息。
床里那女子还在酣睡,已被红狐点了昏睡穴,就算打雷也不会醒来。红狐看着她,不禁想起以前的自己。她把袍子抛给他,用哪种惋惜而凄凉的口吻说道:“还是穿上吧,这个女人是谁?”
“我,我妻子。”
“人之将死,你最好说几句真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睡过一个肩膀上有狐狸的女人!”红狐摘下面具,她恨不能把自己的脸撕下来。
“是你!”他所受的震惊远远大过他对死亡的恐惧,他甚至已感觉不到恐惧,他觉得这实在太荒唐可笑,中邪般大笑道,“是你小狐狸,竟然是你。”他****着站在她面前,他感到一种无上的光荣。
红狐忙又转过身,突然想呕吐,她全身在痉挛,声音也在发抖:“把衣服穿上。”
“小狐狸,你装什么纯哪,你那股骚劲儿哪去了,你不是要杀我吗,你来呀,啊——”
那狂放的侮辱突然变成了沉闷的吼叫,还有骨头粉碎的声音,肉被撕裂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仿佛猎狗在吃食。
红狐转身去看,那人的胸膛里竟然穿出一条黄金的手臂,他长大嘴巴无法呼吸,双眼向外翻着,脸色惨白,赤条条的身子被血染红,仿佛是一个红烛做成的蜡人。她只觉的天旋地转,猛的跪倒就狂吐起来,痛苦的要死。
一个中年妇人忙扯过床上的被子来裹住红狐,轻拍她的后背。那黄金手臂从那血窟中抽出去,红烛蜡人栽倒,现出一个铁塔般的汉子,脸色黝黑,神情阴沉,就像是传说中的金刚,他双臂****着,用那袍子擦臂上的血。
这中年妇人心疼红狐道:“傻丫头,你何必又作践自己呢,过去的事不都过去了吗!”
红狐几乎把肠胃吐光,她感到自己的肠子似乎已绞在一起,她靠在那妇人身上,边咳嗽便大口喘息着,她不说话,闭紧眼睛,只想能睡死过去。
中年妇人看了那汉子一眼,二人间的默契已无需言语。汉子向上一蹦就把屋顶打穿个大洞,妇人把红狐当成是婴儿,用被子把她裹得紧紧的,抱着她从那洞中飞出去,由那汉子开路,跑回玉梨湾。
红狐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那妇人和那汉子都已不在,她不关心他们去了哪儿,把他们留下的美餐吃的一点不剩,然后又睡过下午,到晚上时就去杀下一人。
他自知要死,所以就等待红狐,还备好了茶,想与红狐“品”道。有种智慧叫辩论,有些智慧源于辩论,所以有论剑的说法,而道,也应该用“论”的好,不过“品”道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红狐不善茶道,更不精通什么乱七八糟的“道”,在她认为道就是剑,剑就是道。人们用哲学来解释和研究道,却误入歧途,越说越乱,结果用长篇大论来解释本来很简单的道理,最后就不知所云,干脆就不了了之了。
他先说了一大推红狐不感兴趣也听不懂的话,思绪混乱,言语混乱,逻辑混乱,本想口若悬河如长江流水,中途却拐了好几个弯,又碰上几处绝壁、峡谷,差点被堵死,后来引经据典糟践古人,好不容易才冲出个突破口,找到出路。
红狐实在听烦了,这要换做以前她非要臭骂那孙子,唯一可以聊以补偿的就是这人煮的茶确实好喝。
红狐也学着对方的样子品茶,却多少都带着点“酒”味,那人不不耐其烦的教导她,还亲自做示范,就差手把手了。
红狐喝了好多茶,喝到后来只觉得每一种茶都像喝水,“品道”的过程中她只是听着,一句话也不说。
那人渐渐没了词,便把方才没有解释清楚的道理又重复解剖一遍,“品道”的兴致也渐入低潮,不再那么自我陶醉、慷慨激昂,并且开始表现出恐惧,那黑珍珠般的眼睛里也闪露出一种阴邪,终于他说道:“你真是有耐性,还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么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