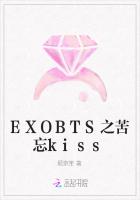“营养不良,加上重感冒,应该让他好好吃饭。”
嘉升请来的医生深更半夜从梦里被吵醒出诊,他诊断富家子李政基所患的疾病却是这么贫寒的病症,如此可见,这人这几天都吃了些什么东西啊。
刚开始煮拉面,他说那是“狗食”,不肯吃,给他做拌饭,他说那是“猪食”,给他弄蛋炒,他说是“猫食”,以后他又说我是“僵尸”,我当然是耿耿于怀,干脆告诉他“那你别吃啊”,就再也没有关心过他。
毕竟生活在一起,讨厌也好,喜欢也罢,既然共同生活在一个房子里,总是应该替他想一想吃饭睡觉这些问题的。
哎呀,我连着做了两次拉面,又一顿没一顿消灭了便当、汉堡包、冰激凌的时候,这人正挨饿导致营养不良呢!我羞愧难当,没有勇气去看这个人的脸。而嘉升却用手轻轻敲着垂头丧气的我肩膀,安慰地说:“梦如,没关系的,他没事儿的,这不是你的错。学长从三年前起,一到这个时候就会大病一场,我们都知道的,但如果知道他是住在你这里,我应该事先告诉你的……”
三年前?
到底,这个人三年前出了什么事情呢?
我暗自思考这三年的时间。三年前我都不认识他,哪儿来的回忆啊?
三年前,也就是说一千多天的时间以前,他没有这种病!那到底这个人出了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能令他发疯,身患重病,身体滚烫得像团火……而且还自我封闭,把自己隐藏在沉默之中呢?
但是,我再怎么纳闷,也不能直接问嘉升“你学长是不是神精上出过问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容别人侵犯的圣域,或者说是一踏上就会“砰”一声爆炸的雷区,我自己就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深深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离开了不像房间的卧室,去找医生询问今后的注意事项,狭窄的小屋里只剩下躺着人事不醒的李政基,还有嘉升两个人了。
嘉升蜷缩着身子,在躺着的学长身旁坐下,默默地看着昏睡的学长的脸庞。可能是降了温的缘故,李政基的脸色又回复了往日的光彩。在嘉升的眼中,学长垂着长长的睫毛,闭着眼睛,这张面孔真是非常平和,而且不知怎的,平和得有些陌生。
在嘉升的记忆中,学长是个异类,他总是认为自己宽敞豪华的家是监狱,梦想从那里逃走。嘉升无法了解大自己两岁的学长到底是怎么想的。三年前的“那件事”夺走了学长的灵魂之后,而身为好朋友兼学弟的自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彻底地无能为力,如同他的父母亲一样。
“嗯嗯……”
不知道是不是鬼压身了,李政基全身满是汗水,他翻了个身,嘴里发出了“嗯”的声音。只有在失去意识的这一瞬间,李政基才无法隐藏自己的疼痛。
“嗯”声过后,李政基接着小声呼唤着谁的名字。
“振宇啊,不可以!”
听到这个声音,嘉升的表情凝住了,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听到他叫振宇这个名字,隔得太久了,他几乎都快忘了还有一个叫“崔振宇”的朋友,也是他的学长,以至于嘉升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三年前,他嘉升,学长和振宇参加了一个登山社,大家休假嘛,所以跑去爬埃佛勒斯峰,当年他们一同随着一群美国登山家上路,一行人十余个全数攻顶成功,可是才离开顶峰不到一小时,那个振宇学长就因为滑倒而受伤,严重骨折。
只要是登山者都知道,知道攀登世界高峰时,一旦有人受伤,大家必须将伤者留在原地任其自生自灭,不许抢救。
这是高山守则,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
如果在连一个健康的人都难以生存的环境下试图运伤者同行,只会连累所有的人一起陪葬。
很多征服过高山大川的人,都有失去队友的创痛,李政基是其中一个。他们一起挑战过海峡急流,感情很好,但在那次挑战中失去最好的朋友。
虽然人无法对抗面对自然考验的生存选择,但是他仍然不好受……对玲玲的内疚,还有,好友的思念。这三年来,李政基无时无刻都在承受这样的自我煎熬。
从那时起,他从美国回来,便不再有笑脸,变得冷漠阴沉,却对风铃言听计从。风铃,韩风铃,振宇的女朋友。那时风铃已怀孕三个月了,回来时才知道她怕男友分心,临走时没有告诉他,那个女孩想等他回来时才告诉他,没想到等到的却是天人永隔。
嘉升猛然想起,学长的那个三岁的干女人玲玲。今天是小女孩的生日,可是没有父亲为她唱生日快乐歌。
衣架上挂着的生理盐水瓶里流出了一滴滴的药液,它至少可以帮助李政基退烧。可是他心里面的火焰又怎么能浇灭呢?
我从医生那里接过了药,嘉升拜托我帮忙照顾学长,说着说着,嘉升的视线突然落在了卧室门口堆放的购物袋上,我顺着嘉升的视线看过去,明白了他正盯着那些购物袋,顿时,我变得满脸通红。
“那个,今天我和恩京,我们一起去购物来着……然后顺便就……”
“就是那段时间害得你学长得了重感冒”,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
但是,嘉升的回答与我的负罪感毫无关联,他很高兴地回答:“不错啊,这样你就不会穿着牛仔裤参加生日派对了。”
听到这话我不明白。”生日派对?谁的?”
“学长女儿的呀!”
“女儿!”
“对呀,学长没告诉你他有个三岁的女人?”
“没有?”我的声音都颤起来了,三岁?
“哈哈,真是的,也许还来不及告诉你就生病。”
我整个人像被轰炸了般,感觉魂飞魄散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感情终结了,总之以后每次再见到他,无论在哪里的时候,都不需要心跳,不用激动了。因为可以不激动,所以心也就只留下失落了。事到如今,自己又能做什么呢?自己爱的男人已经订婚,将永远相亲相爱地生活着,唯一的这个对我有意思的男人又早就有相好,女儿都三岁了?虽然觉得自己很不自在,但是作为“朋友”,恐怕不是这场病,也许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为止,也永远都学不聪明,被人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