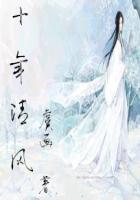丢马的事,对鲁致中来说是鸡毛蒜皮的案子,根本用不着巡察队,尤其是他这个副队长,屁大点的小事,他下面的人,分所的人都懒得管,更别说他这个当官的。他之所以看中这件事,开始,是因为此事勾起了他对自己那匹爱马的思念,后来,他觉得这里面有故事,前因后果并不那么简单。他有些看不透,想不通,要弄个水落石出。
前些年,鲁致中虽然是个放荡不羁的公子哥,但毕竟出身富贵,有钱读书,又走南闯北,虽说没干什么正经事,还是见了不少世面,歪歪心眼比一般人多,琢磨坏事很细致,考虑的也周全。他想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还有他不知情的秘密。刚刚当上副队长,他要在日本人面前露两手,做点有动静的大事,抓几个反满抗日分子,好好整肃整肃街面上的治安,报答日本人的知遇之恩。
顺藤摸瓜,通过马贩子和马市的人,牵出了铁蛋和章家,经过认真分析,鲁致中觉得章家是这件事的核心,其他人都不重要,但马是咋到章家人手中的,一定要弄清楚。
他没有打草惊蛇,先把周围无关紧要的人都摘除掉。马贩子只是为了赚钱,没有什么用处,白挨一顿打,马被没收,买马的钱认赔了,放人。陈家只是个胆小的人,不管他。只有铁蛋,他犯了点难,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要动张翻译官介绍的人,不能不再三思量,要十分小心才是。
铁蛋刚来的时候,鲁致中就满腹狐疑,在鲁致中看来,凭张翻译官的地位和关系,给铁蛋找一个更舒服,挣钱多的差事,应该不是难事,为什么偏偏看上了这个又累又脏的活呢?是不是日本人怀疑他对天皇不忠?信不过他?让翻译官派人看着他?通过张翻译官,把这个小犊子安插在他的身边,作为卧底,暗中监视他?
他想起家父鲁斗金那句话:“莫测高深,高深莫测呀!”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咋回事。
还是小心点好,不能把这个小犊子放在身边,一定要撵走他。公开撵,得罪了翻译官大人,那可不是好玩的,会到大霉。不撵走心里不自在,老觉着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偷偷地在一旁观察了铁蛋一些日子,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是,他就是不放心。
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人不知鬼不觉的让铁蛋自己走了进去。
让张翻译官不生疑,又能达到撵走铁蛋的目的,自己也安了心,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果然,这个涉世不深,不知世事险恶的小牛犊,按着鲁致中早就挖好的大窟窿,铁蛋自己一步一步的走了进去。最终掉进了黑暗的深渊。水桃勾引铁蛋,想方设法让铁蛋吸大烟,都是鲁致中事先挖好的坑,连那位抽大烟的九爷,也是鲁致中派去的。
一切都蒙在鼓里的张翻译官,让铁蛋回家了。
铁蛋被害得实在可怜,稀里糊涂的跳进了陷阱,自己遭罪不算,还给章家人惹来了更大的烦心事。
回到家中,铁蛋犯了几次大烟瘾,气得发昏的艾顺诚,差点没把铁蛋打死。鸣笛十分后悔,几次给艾顺诚赔不是,如果不是他介绍这份差事,铁蛋也不会进这火坑,艾嫂说:
“大侄子,哪是你的不是呀,都是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自己往火坑里跳,再怎么着,也不能干丧尽天良的事呀。他,他怎么能偷你们家呢。我没这样的儿子,咋不死了呢,死了就省心了。”
为了让铁蛋戒掉烟瘾,艾顺诚把儿子捆在仓房的木板上,任凭他哭叫挣扎,也不放他,艾嫂心疼的在房里抹眼泪,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九生和红玉找来了先生,抓了药,给他灌进去。
到了第七天头上,铁蛋好些了。
艾嫂实在忍受不住了,把铁蛋松绑,扶到屋里,他脸色如铁灰,比得一场重病还难受,在炕上又足足躺了三天,才能下地走动走动。身体受的伤害尚且可以忍受,心里的伤痛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平复的。对章家的羞愧,对水桃的怨恨,对父母的负罪感,无时无刻不噬咬着他的心灵。一想到这些,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悔恨自己不如死了,永久闭上眼睛,也就解脱了,向章家,向父母谢罪了。
鲁致中把铁蛋赶走后,自己一个人在章家转悠了好几天,什么事都没发生,也看不出有什么不轨行动和可疑之处。
鸣笛不敢去领马,不领又不行,怕引起分所警察的疑心,那不应了古人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没办法,九生硬着头皮,到西门警察分所,编了一个故事,说这马本不是他家的,是胡子逃跑没来得及骑走,扔下没人管,不得不收下喂着。自古以来,编得最叫人信的故事,在有心人的眼里,细细品味,也总有不对牙的地方。
九生编的故事也一样,没有消除鲁致中的疑虑和追寻到底的决心。
他在章家皮铺暗访了三天,从一个人的口中得知,这户人家三年前,是从双庙子逃难过来的。
“双庙子?那不是我走麦城的伤心地吗?丢马、丢枪、差点没丢命的地方吗!”
这一段经历虽然不光彩,但确实给鲁致中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已过去三年有余,可在他的记忆里那场景依然如昨日发生过的一般,历历在目。想到此处,他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追查章家的来历。
鲁致中找了两个心腹,晓行夜宿赶赴双庙子,暗访章家的来龙去脉。
鲁致中想的很复杂,调查暗访的结论其实很简单,二人没费多大力气和时间就把章家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可是,并没有发现章家有什么不轨之处,老实巴交的买卖人,不富裕,也不贫困。根本不是反满抗日分子,和这个党那个派也扯不上边,本想露露脸办个动静大一点,震惊朝野的大案子的想法落空了。
可是,鲁致中心里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在日本人面前邀功的希望破灭了,但这事还不能算完。彻夜睡不着觉,总有枣红马的影子在脑海里游荡。犬马恋主,鲁致中认为这是他的那匹枣红马,想要告诉他一些事情,所以总在他的心里不愿离去,他问自己,马想告诉他什么呢?很快,他就把马、枪和被打昏的事与章家人联在了一起,这一联,鲁致中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他决定下手了!后半夜,鲁致中带领七、八个人,蹲守在章家的院子周围,等待机会。
天刚刚放亮,整个小镇还没苏醒,章九生第一个起床,走出屋子,打开院门,在门前伸伸腰,活动活动僵板的身子。突然,从背后跳出来二个人,捂住他的嘴,拽到院外。鸣笛出来解手,也被按倒,接着三、四个人冲进屋里,把鸣山也抓走了。
这件事对张翻译官有一些震动!其实,他暗中观察鸣笛和章家所有的人,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按着他的打算,日后,鸣笛也许能有些用处,但围绕他的几个人和几件事还没捋出个头绪。铁蛋、水桃、鲁致中都有一层雾似的,叫人看不透。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铁蛋,嫖女人、抽大烟,盗马,这样一个人和鸣笛是好朋友?和鲁致中是对头?还有水桃,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这些问号就像一团雾,他还没有找到拨开云雾的途径,打开迷宫大门的钥匙。他已察觉到鲁致中是个善于耍手段的人,此人不那么简单,尤其是鸣笛、鸣山、九生被密捕,令他更加警惕,他要小心防着点,不能让这个人咬着自己。
张翻译官本想把鸣笛拉到自己身边,日后成为自己的帮手,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鲁致中,把鸣笛给扣了起来,他必须想办法把鸣笛救出来。然而,他又不能不十分小心谨慎,即要达到救人的目的,又不能把自己牵连进去,所以,他不能直接出面为其说情,只能通过一些关系,间接知会鲁致中要手下留情。
在鲁致中的眼里,张翻译官可以说是个神秘人物,也像罩了一层迷雾,让人摸不清看不透,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接人待物,处理事情的方式,鲁致中都暗中细心的观察过,总觉得和其他翻译官不一样,和日本人也不一样。但是,又说不清、理不透哪儿出现了问题。
鲁致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为日本人当狗腿子,做了汉奸,周围的环境要复杂得多,他要面对日本兵、日本开拓团的移民,还有像张翻译官这种在日本读书、长大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眼里,鲁致中是日本人的狗,可是,在巡察队他又是说话算数的一队之长,他又是鸳鸯楼、逍遥馆的老板。在这么污浊的一池浑水里混生活,要想混的好,混出个人样来,又能保住小命,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不得不眼睛要尖、鼻子要灵、耳朵要聪,时时刻刻防备有人害他,要他的命。
张翻译官对鲁致中来说那就是个大人物,他不敢怀疑,更不敢把自己的感觉说出去,只是因为有铁蛋的事,他不得不小心一点而已。所以,面对张翻译官拐弯抹角的说情,他觉得,虽然他俩都是狗腿子,但是,张翻译官可是日本人的心腹,大红大紫,不是随便就可以得罪的人。他的面子不能不叫鲁致中有所顾忌,生怕弄不好把自己的官丢了,也有可能小命保不住。然而,他太恨鸣笛了,不会轻易放过他,即要给张翻译官面子,又要自己出气。
巡察队把九生父子三人带到鲁致中面前时,他第一眼看到的是鸣笛那双眼睛,似乎在那见过这双眼睛里射出的光芒,是那样深刻,就像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一样,永远也不会忘记。鲁致中盯着鸣笛,心里想到:
不错,就是这双眼睛。在双庙子把我拉下马的,就是长着这双眼睛的人,就是他,不会错的,真是一对冤家呀。时隔三年多,又见面了,这不是天意吗?
鲁致中看看鸣笛的这双眼睛,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目光,就绝对不一样了,鹰扬虎视,目光如炬,这是隐藏不住的,是自然的流露,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认定,眼前这个叫鸣笛的人,就是他在双庙子的仇人。
巡察队刑讯室里,章家父子三人,被吊在房梁上,鲁致中手握马鞭子,在三人面前来来回回的走着,端详着。突然,停在鸣笛身旁,用鞭子顶着他的下巴,说道:
“咱们是老熟人了,没想到吧,三年前你在双庙子把我拉下马。三年后,在我的审讯室里,又见面了,真是冤家路窄呀。你是给我跪下求情呢,还是受用点我这里的新玩艺儿?”
说完用鞭子指指墙上挂着的各种各样的刑具。
鸣笛原以为这次是在劫难逃了,鲁致中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一定知道了他所有的底细。听完了他的这一席话,又不见有日本人在场,直接的感觉就是,问题并不严重,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如果鲁致中知道他杀日本人的事,在日本人的眼里是极为严重的,那是******,这种案子是不会让鲁致中插手的。所以,鸣笛认为,鲁致中除了要消除心中的怨恨,知道的并不多,日本人也没有掌握他的事情。因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说道: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我的怨恨咱们两人清算,把我爸和我大哥放了,他们没有得罪你。”
鲁致中笑笑说:
“还算是东北爷们,骨头挺硬。你想得挺美,可没那么便宜的事。古人都知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你是我的仇人,能放过你的家人吗?”
鸣笛说:
“你说我是东北爷们,没错。爷们就应该有爷们的气度和胆量,办事也得让人瞧得起,不能像娘们似的,小肚鸡肠,一点也不讲究,不砍快。”
鲁致中笑了,说道:
“呀哈!有两下子。有种,长架把式的不能蹲着撒尿。来人,把老章头和他大儿子放了,我和这小犊子单挑。”
过来两个人,把九生和鸣山放下来,鲁致中说:
“谁让这老东西生了个不懂规矩的王八羔子,也让他长长记性,抽十鞭子。”
走到鸣山面前说:
“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瞧那副水裆尿裤的熊样,也抽十鞭子。让他记住,来到我鲁大爷面前,识相点。”
二人被打得嗷嗷叫,放回家去。
鲁致中搬来一把椅子,坐在鸣笛面前,嘿嘿笑着说:
“现在只剩下咱哥俩了,你说吧,怎么过招?”
鸣笛心里骂道:
“这个狗汉奸,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老子早晚收拾你。”
鲁致中说道:
“小子,不是三年前在双庙子大路上啦,现在落到我的手中了,低头下跪求饶,我放了你,咋样?”
鸣笛明白,鲁致中心里这口气不出,是不会放过他的,不如激他一下,早点结束这种局面,因而说道:
“你简直是条疯狗,谁都咬,也不怕损了阴德。”
鲁致中大笑起来,说:
“阴德是什么东西,爷爷我不想要。来人,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扒了他的衣服,裤子也扒下来,扒光。”
被扒光的鸣笛绑着双手,按倒在地上,鲁致中抡起鞭子,暴打起来。鸣笛疼痛难忍,在地上翻滚,咬紧牙关,用绑着的双手护着脸和头,心想:
一定要挺住,挺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只听他叫了几声,便昏了过去。一桶凉水顺头泼下来,红色的血水流了一地,鸣笛依然没有苏醒过来。
鲁致中也有点累了,三年前的那口闷气也消了一些,吩咐道:
“叫他的家人收尸吧。”
巡察队的人,把血呼啦的鸣笛拖到院子里,派人知会章家,把人领回去。鲁致中心里明白,碍于张翻译官的这层关系,他下手虽重,但打的地方都不是致命的部位,即不会有生命之虞,也不会致残。出口恶气就行了,不再深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