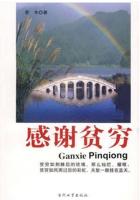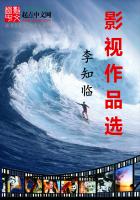第一节 “雅人韵士而故俗其名”
姓氏是公共的,名乃自命也,号则指人名字之外另起的称号。名与号可有也可无意义上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姓名观和谱牒学以及当代人类学和符号学的原理认为,“名号”是一种语言符号,“命名取号”是一种基于社会、民族或者个人自觉的文明行为,名号艺术能够折射出社会、民族或者个人的心理、志趣、追求等,具有重要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意义。清初的李渔作为一介布衣文人,尽管生活经历特殊,然而却多才多艺,最终跻身于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化家之列。迄今为止,李渔的诸多文学思想及其独到见解依然具有难能可贵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借鉴价值。毫无疑问,李渔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所构建的文学思想,无不受到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淀雄厚的审美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从李渔名号艺术的角度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一、取名显志,改号易心
李渔原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又曾说:“男子生兮,弧矢四方”。【1】古人有名有字,还有号。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古人的字是尊辈代取,而号或叫别号、别字,往往是自取。李渔最初的名号表明他早年在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影响之下,渴望顺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走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一种遵长辈之命类神仙下凡建功立业的勃勃胸襟和理想抱负。明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在浙江婺州参加童子试,一举成功,受到主考官浙江提学副使许豸的高度赏识,称赞李渔为“五经童子”。可是,李渔后来却应乡试不中。不过,李渔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渔再次应乡试,孰料适逢甲申国变,半途而废。明清易代的战火彻底焚毁了李渔科举仕进的美好人生理想。明朝失政,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一连串的巨大世变接踵而至,迫使李渔重新选择人生道路。时近中年的李渔面对黯淡前途,决心买山归隐。1648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李渔于家乡伊山头盖起了一座伊山别业。李渔匠心独具,设计精妙,建成了不少因地制宜的风景点,取名如燕又堂、停舸、宛转桥、蟾影、宛在亭、打果轩、迂径、踏响廊、来泉灶等等。这些风景点的名字叫得美丽动听,其实大多因陋就简,甚或有名无实。由于李渔善于苦中作乐,点铁成金,因而诸多风景点命名显得别致雅趣,诗情画意陡然倍增。与此同时,李渔自己也易名改字,名渔,字笠鸿,号笠翁,表明了归隐山林渔樵生涯的心迹。李渔在《张敬止网鱼图赞》中自我解释说:“鱼我所欲也,因自名笠翁。以其才薄劣,于世无所庸。人地务相宜,所以泯其踪。”【2】李渔在《卖船行和施愚山宪使》中也慨叹地说:“嗟我一生喜戴笠,梦魂无日去舟楫。谁料人间张志和,惟向口头营泛宅。四海人人唤笠翁,笠翁其名实则空。一竿无可置身处,倩人作画居图中。”【3】张志和是唐代著名词人,初名龟龄,字子同,婺州(今浙江金华)人。16岁游太学,擢明经,向肃宗上书陈策,受赏识,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赐名“志和”。后因事获罪贬南浦尉,遇赦量移,遂不复仕,浪迹江湖,自号烟波钓徒。又自号玄真子,著《玄真子》12卷,3万言;《述太易》15卷;均佚。张志和能书善画,长于音乐,现存《渔歌子》即《渔父》词5首,写江南景色、渔父生活,其一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李渔把自己与同籍贯而且志趣相合、才华相似的唐代词人张志和绾结起来,并且以张志和自况,写出了在时世面前无可奈何的隐逸者的情怀。从李渔的改名易字,不难看出李渔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事实的确如此,明清鼎革之后,李渔放弃了仕途追求,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走上了一条亦文亦商的道路,进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此后,李渔在不同的时期又署别号伊园主人(1648年,据诗歌《伊园十便》小序)、随庵主人(1655年,据黄鹤山农传奇《玉搔头序》)、觉道人(1658年,据杜濬小说《十二楼序》)、觉世稗官(1658年,据小说集《十二楼》署名)、笠道人(1658年,据小说《闻过楼》第一回)、莫愁钓客(1668年,据传奇《巧团圆》批评署名)、湖上笠翁(1671年,据《闲情偶寄》署名)、新亭客樵(1680年,据《芥子园画谱》初集《青在堂画学浅说》跋)等等。古人的别号往往是两个字,但也不排除三个字或者三个字以上。例如,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汪道昆,字玉卿,号高阳生;陶潜自称五柳先生。尤其是唐寅以惊语多字命名,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古代从春秋战国时起就产生了别号,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号,唐宋时期取号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时期别号艺术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人往往取数个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古人取名号往往还有一定的涵义,如梅鼎祚晚年号胜乐道人,与其一生不得进仕有密切关系;沈璟选择曲学和戏曲创作为他的终身事业,自号词隐生,表明了他的人生志趣。李渔所取别号遵循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名号文化,同时,其别号皴染了以高就低、以雅就俗、脱略世故、超然物外的鲜明思想色彩,有着浓郁的道教和佛教的意味。具体而言,“伊园主人”、“随庵主人”、“觉道人”、“笠道人”、“新亭客樵”等采用了近义式言志法,灌注了道教远身避祸、崇尚自然的内涵。“觉世稗官”则采用了近义式托寄法,明显地受到了佛教关于心性本觉、去掉妄念的教义影响。而“莫愁钓客”、“湖上笠翁”则采用了互补式言志兼托寄法,既有道教归隐山水林泉、寻求内心的平静与自省的思想色彩,又有佛教注重性静、消除烦恼、寻求解脱世俗的思想色彩;相比较而言,后者胜于前者。毫无疑问,李渔别号“莫愁钓客”、“湖上笠翁”的来历与柳宗元的《江雪》有内在关系,受佛教影响明显。柳宗元的《江雪》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叙事、写景当中暗寓禅家生命与自然因缘而生、本空无有之理。而李渔编辑出版的《四六初征》卷八有陈淏《贺笠翁六秩举第六子》一文,曰:“果然芥子园中,须弥可纳;行见一房山内,玉笋同班。十年前孤舟蓑笠,何期此际,绕膝尽可钓鳌;五秩时独对寒江,孰意阶前,指口群堪射虎”。【4】陈淏将柳宗元的《江雪》和李渔的别号两者联系起来,所言极是,可谓李渔的知音。明清时期,儒、道、佛三教合流蔚为趋势,影响广泛深入世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李渔以一介儒生的社会角色亦文亦商活跃于世,而又绝意仕途,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游刃有余,我行我素,生活虽然不乏艰苦却往往自得其乐,所取道教和佛教意味浓厚的别号特色显著,趋时尚,重形式,正是其悟道自觉觉他、超越世俗心态和追求精神自慰的客观反映。
二、性癖自为,特立独行
当然,李渔并非一般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儒生或道士或佛教徒,也非通常古代文化意义上的隐逸者,而是有着近代文化创新意识和鲜明个性的人。李渔在明代中期以后蓬勃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的触动下,不愿因循守旧,刻意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礼法行为的拘囿,向往和努力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道:“予性最癖,不喜盆内之花,笼中之鸟,缸内之鱼,及案上有座之石,以其局促不舒,令人作囚鸾絷凤之想。故盆花自幽兰、水仙而外,未尝寓目;鸟中之画眉,性酷嗜之,然必另出己意而为笼,不同旧制,务使不见拘囚之迹而后已。”【5】李渔希望让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高高飞翔,说:“予性嗜禽鸟,而又最恶樊笼”;【6】李渔深谙“丈夫成名当自立”【7】,渴望依仗自己的才能立言扬名、光宗耀祖,但是,有感于“数奇于儒”【8】,迫不得已投身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卖文以糊口养家;对此错位屈才,李渔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李渔曾在《鸡鸣赋》中假借替鸡鸣不平曲折地抒发了内心的怨恨,说:“鸟之以声事人者众矣!要皆进谀献媚之口,非振聋启聩、助勤警怠之音也;惟鸡则然。……予欲特书其功,以补前人之未逮,或曰:‘贱物耳!焉用赋之?’予曰:‘匪贱也,为多屈耳。使天能爱宝,偶然一生,则在外必贡于朝,在四译必献中国,能使神鹊失灵而凤凰不得称瑞者,必是物也。贱云乎哉!’”【9】中国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李渔一人取了至少八个别号,基本思想内涵不仅在志向和情趣趋于一致上,而且从数量众多上来说,都凸现了崇尚唯才是用、自主自由地抒发情志的精神个性。
李渔于顺治七年(1650年)远离家乡,后来分别迁居杭州、金陵等地,上无片瓦,下无锥土,携家带口甚或包括主要由妻妾组成的家庭戏班在内近五十口人,凭借文学艺术创作成就,一生出入“大人之门”,不时过着普通布衣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优裕生活。对于这种生活,世人议论纷纷,羡慕者有之,理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侮辱者有之,讥嘲者有之,诅咒者有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李渔因此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惯于“打抽丰”的名声。然而,李渔自己是怎么看的呢?李渔63岁游京师时,在自己的寓所门框上贴有一副自撰对联:“绣衮丛中衣褐士,少年场上杖藜人”,横批是:“贱者居”。面对世人的鄙薄,李渔干脆自我命名曰“贱者”,这一自号就是李渔当时生活和思想的写照。是得意,是抗拒,是怨怒,是自嘲,是委屈,还是悲哀?似乎各种感情因素和思想成分兼而有之。李渔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生活,也没有否认自己的真实思想,而是袒露了自己的真实个性。对于世人的态度,李渔实际上早已有所预料。李渔在《赠吴玉绳》中说:“我性本疏纵,议者憎披猖”。【10】李渔在《读史志愤》中还说:“我无尚论才,性则同姜桂。不平时一鸣,代吐九原气。鸡无非时声,犬遇盗者吠。我亦同鸡犬,吠鸣皆有为。知我或罪我,悉听时人喙。死者若有知,未必阶之厉。”【11】可见李渔对世人的妄加置喙采取了一种悉听其便的漠视态度。李渔惯于“打抽丰”,在品行上的确有可议和瑕疵之处,但是,实事求是地透视一番,其中不无些许道理。因为,实际上,李渔与达官贵人交际往来,论文赋诗,酬唱观戏,往往收获不少实惠。具体地说,一是因为只有达官贵人才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消费得起李渔创造的精神产品,这符合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客观规律;二是因为大多数达官贵人较高的文化修养有利于通过相互切磋提升李渔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的水平,这符合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客观规律;三是因为达官贵人给李渔的钱财馈赠和生活待遇是李渔一家人得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之一,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规律。李渔甘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务砚田糊口之实,而不愿意为了应付世人的不一杂说务耗损生计之虚,纯粹是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使然。因此,诚如李渔在《福橘赋》中所说:“雅人韵士而故俗其名者,名以人重,人不以名重也。”【12】
随着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成就的与时俱增,李渔在文坛上的名气逐渐扩大,但是,无论如何,毕竟终生没能踏入仕途。对此,李渔情结于胸,郁结于怀,潜沉内心的初衷难于磨灭。李渔老年得子以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李渔在《名诸子说》中解释自己为儿子们取名的用意说:“予生七子而夭其二。长曰将舒,次曰将开,三曰将荣,四曰将华,五曰将芬,六曰将芳,七曰将蟠。……诸子命名皆从‘将’,将者,将然未然之词也。天下事莫妙于‘将’,而莫不妙于‘既’。既,则令人观止矣,曷若将然未然之多余地乎?吾欲诸子顾名思义,人各用将。凡事皆然,不独功名富贵。富而不将,则以满致溢;贵而不将,则由高得险。戒之哉!”【13】由此可见,李渔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不满足于现状,能够通过出仕得到自己所没有得到的功名富贵。读书做官,这是封建社会一般文人士子梦寐以求的理想。李渔自己也承认不能“免俗”。康熙十四年(1675年),已经65岁的李渔长途跋涉从金陵送长子将舒、次子将开回浙江应童子试,途经浙江桐庐东汉隐士严子陵钓鱼台时,不免触发了早年渴求仕进的心结。李渔在《严陵纪事》中说:“未能免俗辍耕锄,身隐重教子读书。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14】回程途中,李渔又作词《多丽·过子陵钓台》一首,将自己与严子陵相比较,再三自责,其中写道:“同执纶杆,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15】这一首词表明此时李渔的思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复。这种观念现象说明,李渔作为一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化人,受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思想不可能是纯粹单一永恒凝固的,在清政府已经站稳了脚跟,社会趋于安定,时代背景与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之时,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会发生相应调整,李渔的思想也相应发生回潮客观上在所难免,何况李渔的初衷就是因为出仕不成而立志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以便立言扬名的。也就是说,李渔毕生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著述以及渴望仕进,在立言扬名这一终极目标上来说,可谓殊途同归,并行不悖,其揆一也。
回顾历史,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此前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身上。汤显祖的晚年是在贫穷当中度过的。汤显祖自己因为厌恶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弃官还乡,但是,却把儿子们的前途寄托在科举入仕上。汤显祖的长子士蘧就是在求学途中病死他乡的。一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月初八浴佛节时,58岁的汤显祖还在睡眠中梦见长子士蘧“持书颇乐,且语地下成进士”【16】。这种情形只能够说明封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当时的任何一个人想要与封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作彻底决裂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殊不知,明摆着的事实是,李渔一直到临终之前,仍然没有放弃文学事业。例如,李渔抱病为徐冶公《香草亭》传奇作序写评,为毛声山《四大奇书第一种》(《三国志演义》)作序等等。这些作为不能不说是值得后人称道的。有的时候,李渔对自己的文学才华表现得非常自信,乃至有些骄傲自负。比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声音之道,幽渺难知。予作一生柳七,交无数周郎,虽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通显,然论其生平制作,塞满人间,亦类此君之不可收拾”【17】;又在《与徐冶公二札》中说:“当世才人,有如星密;文字之富,家拟石崇。若止论传奇一道,则冶公与弟二人之外,不能再屈第三指矣”;【18】甚至把自己与元代杂剧家们进行比较,在戏曲《慎鸾交》中借剧中人物唱道:“【蝶恋花】年少填词填到老,好看词多,耐看词偏少。只为笔端尘未扫,于今始梦江花绕。这种情文差觉好,可惜元人,个个都亡了。若使至今还寿考,过予定不题凡鸟”。【19】李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渔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在文学领域切切实实做出一番世人公认的成就,立言扬名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所以,无怪乎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一再强调说:“务实不务名,此予立言之意也。”【20】值得一提的是,李渔认为寄希望于儿孙们成就功名,作为长辈者理应率先身体力行,为之垂范,而后泽惠年轻一辈。李渔说:“树人如树木,欲为子孙植梁栋,必须为祖为父者浇培灌溉于先,使之日繁月盛,渐有根深蒂固之意,而后遗之子孙,子孙始得其用。未闻剪其枝叶而拔其根本,置之雨露不到之地,候子孙收而植之,而可以为梁为栋者也。”【21】李渔这种家庭教育思想合情合理,其名号艺术蕴含积极的审美文化价值,无可非议,时至今日,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值得人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