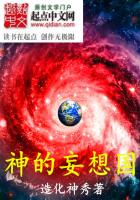何子非遇到孔玉瑶之时,他正准备下朝离宫。
这是他自大理寺出来后第一次与她相见,嘉宁公主穿着繁复而华美的宫装,笑盈盈地望着他,竟有恍若隔世之感。
她似往常般唤了一声,“子非哥哥。”却并不上前。
何子非笑道:“玉瑶。”却也不上前。
分明什么都没变,却又什么都变了。
天朗气清,四下无人,二人相距甚远,遥遥相望。到底是孔玉瑶先沉不住气,“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子非哥哥是怕了我么?”
何子非摇摇头,“不是怕你,而是怕连累了你。”
“这一回,我算是明白你为何避我如蛇蝎。”孔玉瑶今日描眉搽粉,妆容精致,却也未能遮住她脸上接二连三变化的神情。一瞬间有后悔、有尴尬、有内疚、亦有何子非从未见过的决绝。
她清了清嗓子,“是我无知不懂事,险些害死你。”
“错不在你。”何子非似乎并不在意,反而笑问,“短短几日,玉瑶似乎变了?”
“我哪里变了?”孔玉瑶追问。
“从前是不谙世事的小公主,如今是心怀天下的小公主。”何子非打趣。
“从前的我好,还是现在的我好?”她不依不饶。
“都好。”
“我这么好,却有人不识珠玉,一定会后悔!”孔玉瑶撅了撅嘴,含笑的眸子里闪烁着一两点星光。
明媚的日光下,华服的公主宛若盛放的牡丹,美得教宫娥们移不开眼。她目不斜视地绕过御周候的身侧,在几个侍卫的保护下驾车离宫,自始至终与他再未有一次目光的相遇。这一幕在外人看来,仿佛二人是从未相识过一般,又怎会相信先前那莫须有的绯色事件。
何子非望着嘉宁公主远去的车驾,忽然对她心生愧疚,可转瞬之间,那一点愧疚也随着看清不远处高墙之上的杏黄色背影而消失的无影无踪。
巍峨的高墙之上,太子的长袍明亮如金,对着他忽然一笑。
何子非颔首,算是回礼。
若敢肖想驸马,便会死无全尸!
他虽在大理寺想得透彻,却不及太子的一个眼神。与他而言,若想在陈国立足,最好的出路莫过于尚公主。何子非虽明白此理,却从未想要这样做。
公主的辇车一出宫门,直接往鸿胪寺方向而去。诸侍卫得到吏部尚书齐皓密令,一天十二个时辰保护公主安危。说起齐皓,分明已经官拜吏部尚书,却还兼任着兵部侍郎一职,有眼力之人皆知他深受皇帝信任,今后前途无量。
此时,周太子已下榻鸿胪寺,由玉王殿下亲自设宴款待。知言跟在玉王身侧,便有机会时时观察这位周太子,虽说何岑与何子非是堂兄弟,可周太子却与御周侯并不相似。
御周候何子非身长而挺拔,眉目清而英俊;周太子何岑清瘦而文弱,美姿仪而典雅。这位周太子也算是个奇人,既不像陈太子孔诏那般王气逼人,也不像玉王孔轩这样温和暖人,更不像御周候何子非那厮——虚与委蛇!
稳而不躁,贵而不骄,美而不妖,今日一见的确值得。
知言不由笑着点点头,却见周太子身后有一鹅黄裙裾的妙龄少女,怒气汹汹地盯着她。
女子那娇俏愠怒的眼神,却看得知言一个哆嗦,那冷冰冰的模样,倒与韩霖有几分相似。知言连忙移开眼,去见有厅外有几名官员交头接耳,似是焦急地说着什么。
玉王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点头示意知言去处理。
她草草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微微皱眉。原来是公主的马车在来鸿胪寺的路上被人截在半路,而截车的不是旁人,正然是黎国的太子凌柯。难怪凌柯多日以来毫无动静,原来是把主意都打在嘉宁公主身上了。
待知言赶去之时,只见那马车流苏低垂,八位御侍带刀分列周围。与此同时,有一男子红袍似火,正一动不动地蹲在车顶上,调笑道:“说了这么久,公主还是不肯出来让我看一眼么?”
马车里的声音带着十足的愠气,“大胆狂徒!”
御侍们面面相觑,此人乃黎国太子,没准是今后的驸马,他们到底该如何是好?
知言自知终有一日会与凌柯一见,却未想到是此时此刻。凌柯是黎国皇帝凌桑的长子,也是已故皇后许云暧名义上的儿子。这么说来,他应该是她的兄长?不对,从辈分上来说,他应该叫她一声姑母!
这么一想,知言险些从马上栽下来。她努力让自己气定神闲地下了马,正了正衣冠,朗声道:“鸿胪寺少卿许知言,特来迎接黎国太子殿下。”
凌柯的目光瞬间被这个穿着官服的英俊少年吸引了去,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带着莫名的惊喜“你就是许知言?”
“正是下官。”
凌柯自马车上一跃而下,“我看一眼公主就走。”
“登徒子!”车里又传来了孔玉瑶的暴怒声。
“你们陈国人,都是这样骂人的?”凌柯双手抱在胸前,浓密的眉毛扭在一处。
“殿下息怒,公主待字闺中尚未出阁,您此举的确不合礼数。”知言答。
“礼数?什么礼数?”原来凌柯并非有意挑衅,实乃不懂这陈国嫁娶之礼。
“本应该是两情相悦之事,您却胁迫公主殿下,谓之不合礼数;公主择驸原为公平竞争,诸国贵公子皆下榻鸿胪寺,唯独您要率先与公主相见,有违契约,亦为不合礼数。”知言一一解释。
不想黎太子听罢,频频点头,“你说得有理。”转而隔着轿帘向马车内的女子道:“你若是好好跟我说话,我早放你走了。”
说罢便听那马车里咒骂声起,“哼,做梦!”
太子凌柯笑着上马,与鸿胪寺少卿一同离去,“我听说陈国女子多美貌,料想公主必定是最美的,便想见上一面,当真是无心冲撞公主。”
“殿下多虑了。”知言笑道。
“不多虑,嘉宁公主究竟如何?比你还美吗?”凌柯问。
随行的一干官员闻此,都窃笑了起来。
“太子殿下。”知言环顾左右,缓缓道:“在陈国,不宜用美来形容男子。”
哪知凌柯听罢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陈国人真是有意思的很。”此刻两匹马走得极近,凌柯也不顾左右有人,兀自伸出手捉住了知言的衣袖,“你转过来让他们瞧瞧,我说错了吗?哪一点不美?”
凌柯在黎国诸皇子中稳坐太子之位,知言原以为他是个城府颇深之人,谁能料到他竟然这般无理取闹,愁得她直翻白眼,“殿下,您这样拽着下官的袖子,恐怕会被人误会。”
那人便更加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又能有何误会?”说罢,便在鸿胪少卿大人纤细温暖的小手上捏了一把。
知言大窘,连忙收回了手,摊开掌心,那里正躺着一枚精巧的长命锁。正面是个工整的“福”字,一旁还刻着个小小的名字,月微。翻面来瞧,一个个细致巧妙的文字映入眼帘——恰是她的生辰八字。
她心中微动,在掌心轻轻摩挲着那枚长命锁,却高高扬起脸来,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匀称。
太子凌柯忽然收敛了笑容,端坐在马上,厉声道:“许大人这是什么态度?看不起本殿下么?”
之前还在腹诽凌柯毫无城府,无理取闹,知言这才意识到,方才的种种原来都是假象。此人的头脑极其灵活,反应尤为快,既然如此,她便陪他演这一出。知言冷笑道:“岂敢,下官不是这种人。”
“还说不是,我看你就像!”
众臣跟在二人身后,看不真切他们的面容,却听得二人一来一回各不相让,倒是吵了起来。
“像?”知言疑惑,“哪里像?”
“眉眼身量,哪里都像。”凌柯擅骑射,此时在平路上骑马可谓如鱼得水,他懒洋洋地将双手抱在脑后,任凭胯/下的马儿兀自散漫游走。
原来凌柯一直都知道她是谁,可是却碍于在众人面前,无法与她单独相处。他这看似厌恶实则亲密的态度实在是高招!轻轻松松瞒过了一干下臣的猜忌。
一回到鸿胪寺,凌柯便在玉王面前告了鸿胪少卿许知言一状,说她对自己多有怠慢。
当夜,知言依旧不能明白凌柯此举为何,于是翻来覆去道:“你且说说,为何有人无冤无仇,偏偏要诋毁你厌恶你?”
叶舒正替她扇扇子纳凉,忽然一顿,漂亮的柳叶眉皱成一团,“大人都看出来了?”
答非所问,必有内情。知言唇角一勾,连忙道:“嗯。”
“我不过是无心之失,也不知是怎么开罪了他。”叶舒为难地嘟囔。
“他本不是善茬。”知言稀里糊涂接了一句,大抵猜到了“他”指的是谁。
“我知道。”叶舒面露难色,“所以,我想……今后余大人来访时,我还是回避罢!”
知言的眼睛滴溜溜一转,忽然明白过来。自她调任至鸿胪寺,白天很少回府,连余鹤大人的鬼影都未瞧见。可是看到叶舒为难的模样,倒像此人日日拜访,对她多有刁难。
二人正在闲聊,忽听得一个冰冷干脆的声音道:“看茶。”
知言瞧着叶舒浑身一颤,吓得不轻,听到余鹤的声音,泪眼汪汪地望向她,“大人……”
余大人前脚迈进书房,便看到许知言躺在软榻之上,身后巴掌脸的小女子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
“你也在?”余大人面不改色地问。
“余大人前来,怎么也不叫人通报一声!”知言坐起身,神情不满,转而轻声对叶舒说:“你先回去。”
叶舒瞟了自家主子一眼,心知知言这回肯定会护着她,满面笑容地跑了。
余大人撩袍入座,面色泛黑。
“余大人此来有何贵干?”知言明知故问。
“要人。”余鹤答。
“谁?”
余鹤不屑地看了她一眼,“叶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