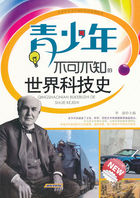十五
杜月和拿了一块银元到村前小杂货铺买糖块,开这铺的钱财富竟笑眯眯地问他:“听讲你很爱拿你姐姐用过的经血纸来玩,是不是?”
“才没哩,我哪时玩过。”杜月和矢口否认,但却在一瞬间里闹了个大红脸,待钱财富给了糖块他他就快快离开了这儿。
走得很远了,背后还有只言片语灌进他的耳朵,似利箭一般扎进他的心,叫他到了没人的地方时耳朵仍嗡嗡地响着,思想几乎让羞耻感弄得自己停止了活动。
他没有马上回村去,怕别人也会这样取笑他,因而便一边数着自己手里的糖块,一边走向左边山的方向。在以前,他的心的空间可以说是单纯而坦荡的,没有什么杂质的,可现在他却感觉他的心象眼前不时下陷的泥土一样,很多地方乌脏而不再那么平整了。
到了离山很近的地方他才剥糖,正要吃第一块时,他忽然听见附近有铁锣响,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队头扎白巾的人从柴尾岭村方向走来,走向左边山的方向,他们中,撒纸钱、烧鞭炮的,和抬花朵织成的花环的人走在前边,红漆棺材随后,然后是哭葬的、送葬的跟在后边,其中有两个女人很会哭。在她们的心中不见得会有多么悲伤,但她们哭出来却给人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因而哀号响彻山冈。
杜月和对这种事儿是很感兴趣的,看同村有男孩儿向这些人跑,他也跟着跑,但才跑一会儿他就收住了脚步,转回村里去。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会把死人抬到哪儿葬。从装死人的棺材看,又高又大,还雕饰得很精美,不象是平常人家,而是有钱的,或在外边当官的人家。这样的人家对埋葬地的风水是很讲究的,有可能会抬到很远的地方去埋。而且这种时候虽还有春风拂面,但给人感觉天气已挺热了,跑一跑后背就出汗,而他不想出这汗。
他回到村口,见杜良键和钱金宝正在那儿议论着送葬的事儿,只听钱金宝说:“就算做上再大官,挂上再大招牌,脱了衣裳,光了脊梁,都是一个样。”
杜良键附和他的话儿:“怎么不是呢。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贱,这么脆弱,有的昨日看着还好好的,今日就突然不在了。”
“所以我讲,象我们这样的人,不用跟人争什么,有两口饭吃就得了。不然你跟人争,到头来象柴尾岭的这个温新增,当到县老爷又怎么样,还不是四十岁不到就死了!”
杜月和知道他们两个是最爱说人闲话的,怕他们也拿自己探究姐姐那些月经纸的事儿来取笑自己,没敢走近他们,低着头快快进了村去。
此时在杜月和家里,一张桌子上的盘子里有两块芝麻糍。杜月雨端了盘子站到门口吃。在这柴头岭村,绝大多数人家一年到头都是吃不起一次芝麻糍的。她自己现在吃着,心里想着那些比自己家破烂得多的房屋,心中生出了怜悯之心。
杜月和嘴里含着块糖回到了家门口,姐姐他没看,却去注意钱成山家。自从那日办喜宴见到钱成山家的新妇后,杜月和老是心栖栖的,老想着那美人儿,很希望能再碰见她。但她总不见出门,只有哭声从屋里传出来,叫他怎么也碰不到。
现在他这样往钱成山家门里望,如果那美人儿从屋里走出来或在厅屋里干些女工,照一般情形说,他应该能看见她,可他这么多日就是看不见。
甜甜的糖的汁水从他嘴里含的糖块里溶解出来,咽进了他的喉咙,顺着食管流进了胃囊。
“你在人家门口探头探脑的干啥啊?”杜月雨瞧着他,似有些阴沉着脸儿。
“哦,我,我……”杜月和给她问得有点儿羞臊有点儿心发慌,结舌了一下后,他突然灵机一动,撒了个谎,“我不看什么。我听见他们屋里好象有猫叫。”
杜月雨又是气又是恼:“你看猫!到哪儿能看得到猫!刚才想叫你去喂牛也找不见你,也不晓得你去哪儿干了什么!”
“我,我,我去上茅寮了。”他又撒了个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