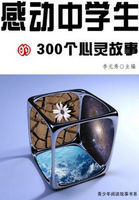十九
小暑到来后,柴头岭村出现了持续的高温无雨天气。光阴在指尖一点儿一点儿地流逝,大地上的水叫阳光一点儿一点儿地吮饮。每日里陈云彩都见自家池塘里的水一点儿一点儿地少下去,开始只是露着堤围,接着就露出了堤围下的泥,再接着那泥又越露越多,直到后来只剩下了不到十米宽的水。既然池塘里已快没水了,那鱼虾都挤到了塘的中央,自己不捞起来,别人也会在晚上偷偷摸摸地跑去抓掉。
一条鱼就值好几块银元,是损失不得的,得抓紧时间叫人给捞上来。这事儿好办,他们平常有什么事儿都叫惯了杜源宗的,现在就也叫杜源宗。杜源宗很痛快,一叫就来。这杜源宗做什么事儿都有头脑,捞鱼也一样。尽管池塘里水已不多,但他也不直接下网去捞,说那会漏失一点儿小鱼。因此他脱光膀子,露出被烈日晒黑了的上身皮肤,先用木桶一桶一桶地把水提出去,但他又不把这水直接倒掉,而是挑到他家菜地旁的一个小池塘里倒进去。这样来来回回地多跑了很多路程,但他却一点儿也不嫌累。
待池塘里的水提出了三分之二,那鱼就挤在了一起,杜克勤一家大小拿了筐啊、桶啊的一条条把它们抓起来,撂进去。
抓鱼是愉快的,但驱赶围观的小男孩、小女孩们却很烦人,因为他们会在什么时候趁你一个不注意,就悄悄把你一条不大不小的鱼儿偷了去。
杜克勤发现有鱼少了以后,一见小男孩小女孩们围上来就很上火,大声地骂,把声音也很快骂哑了。
天气热,鱼得赶快卖掉,不然很快会死掉发臭。
好在养鱼的人少,不用挑出村,先给本村的人买去了一半过,再把剩下的拿到乡里卖,只用了大半日功夫就卖完了。
抓完了鱼还得把莲藕也挖出来,不然不是给人偷,就是烂在塘里。
这莲藕是没种够时候,根茎都还不大粗。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水都干成了这样,池塘快没绿滴,浆液也快没银光,只要可以吃就行了。
同样河道里也已快没水了,这时鱼也好摸,田螺也好捡。很多村子里的人都跑到河里去搅浑水,争抢,钱金宝和杜文重两个还为此打起架来。
光线从窗子里射进了屋,淡淡的灰尘在光柱里浮动着。
陈云彩在光柱当中站着对镜梳妆。光柱和屋子里的暗影产生的反差使她的模样儿显得颇为古怪和奇特,她看着看着,自己突然忍俊不禁地咯咯笑弯了腰。
梳妆完后,陈云彩就撑着红色的油纸伞来到了河边,看谁捡的田螺多、靓、大,她就向谁买,看了半日她才买了一斤,回到家拿刀去切那田螺,满难切的。
张兰娇脸上带笑,凑过来说:“姐姐,你拿铁钳子切,那样会容易得多。”
“是吗?现在我就去拿。”她说,走去找出铁钳子,用它切田螺,果然容易得多,每一个田螺,不用费多少力气,轻轻一切就切下了尖头。
由于天气连续地旱,村民们昼夜担水浇地。有几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儿,身子还远没长成哩,也用那瘦削的小肩膀挑着木桶去担水,有的压得走路一歪一歪的,有的则弓着腰,弯着背,都显出很辛苦很费劲的样儿。
张兰娇给父亲喊回家,和爸妈一起去挑水,只没让她弟弟张贵荣去挑,因为她爸虽然没上过学堂,却是出去见过一下世面的,知道小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干得太重,是不利于正常发育的。河里的浑水已不多,张兰娇一家不想跟人去争,就回家挑自家井里的。有一次张兰娇挑了一担水刚出门,遇见了杜月雨外公张世昌,张世昌问她:
“你们家连井里的水也挑去浇地,就不怕到时连吃的水也没吗?”
张兰娇瞅了瞅自己的担子,不知怎么回答他。她是没想过这问题的,不过听他那样一说,她觉得很有道理,不由为自家的吃水问题担忧起来,到地里见了父亲就说:“我们家里的水要挑光的话,到时没水吃怎么办呢?”
“顾不得那么多了,要是稻子旱死,到时饭也没得吃,全家人更得饿死!”父亲说。
这时县府贴出了断屠的公告,说是为了求雨,在一月内禁止宰杀任何牲口。
柴头岭村在女人墟旁边晒谷场架起了祈雨棚,由村公所下令各家各户各派一个男人来跪拜、唱祈雨歌、守夜。
陈云彩叫杜克勤去,杜克勤烦厌地说:“唉,哪里祈得到什么雨啊,去也是白去,我很不想去。”
“祈不到雨你也要去啊!要是不去,到时村公所抓你出钱,你损失更大。”陈云彩催促他。
“唉,还不是要你出钱!出力!老是这样烦死你!”杜克勤皱着眉头又道。
二十
第二年离谷雨还有几日的时候,张兰娇就给肚子里的孩子不时踢得颇为疼痛颇为难受了。刚好谷雨那日,肚子里的阵痛感一阵强似一阵,一波紧似一波,总有一种身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往外坠的感觉,就算她是个从未有过生育经验的小妇人,她也知道自己快要生了。
陈云彩比张兰娇还紧张,在谷雨前就日日问她:“要不要去女人墟?要不要去女人墟?”现在见她已有要生的表现了,便心紧地连催她:“走,快去女人墟,快去女人墟!”
一边说陈云彩一边收拾了几样到女人墟会用得上的衣物,搀扶着张兰娇走向女人墟。
接生妇许玉梅给张兰娇和另一个妇人同时接生。另一个妇人的公婆和丈夫穿着都比较破旧,衣服上到处都打有补丁,但温桂珍、刘细娟对她们两位产妇却一视同仁,在旁边忙前忙后,表情关切,说话温和。
张兰娇给送到女人墟后,就给安置在一张竹床上,但她老是生不出来,阵痛使人的肚子很难受。张兰娇痛得眼泪不时流出来,泪痕干了一次又再出现一次。由于她乱动,那两个小妇人钱青霞和杜丽鹃走过来拽住了她的胳膊。
屋里竟反常地热得蒸笼似的。拽住张兰娇胳膊的钱青霞、杜丽鹃满头大汗,张兰娇、许玉梅和另一个妇人也满头大汗。
由于天气已热,就见得到苍蝇了。
苍蝇飞来飞去,有时落在张兰娇的手上、脚上,有时落在她的脸上。落在手上、脚上都叫人不大舒服,更别说是落在脸上了。
她感觉过了很久很久,至少有差不多一日的时间,孩子终于有一点儿一点儿自己往外出的感觉了。当他完全从她的肚子里出去以后,她感觉自己的身子象空了一样,阵痛消失了,整个人舒服了许多。
虽然生的是个女婴,但陈云彩也欢喜地走前来,拍着张兰娇的肩膀,和她着实亲热了一番。
因为女人墟里的条件不适合产妇和婴儿的饮食起居,张兰娇当日生下孩子才隔两个小时,就被闻讯赶来的杜克勤接回了家。
“给伢伢(婴儿)起个什么名字啊?”杜克勤在进门后不久就问陈云彩。
“你读的书多,你给她起吧?”陈云彩说。
“叫杜凤兰怎么样?”
“绕着舌头,土里土气的,不好听。”陈云彩道。
“那就叫杜丽香吧,又好听又不土气。”
“得,得,随你。”陈云彩又说。
这时婴儿哭起来,哭得很高声很尖利。陈云彩叫张兰娇把**塞进她嘴里,但她咂不出奶水来,仍是大声地哭。
陈云彩让杜克勤抱着孩子,她自己匆匆忙忙地跑出去,上卖肉佬杜重生那儿去买点儿肉。要催奶,得补充足够的营养。
陈云彩把肉买回来,赶快就到灶屋去跺成肉泥。
灶屋顶上的烟囱冒出了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