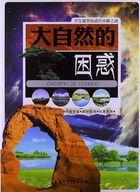四十
村里都在传,钱新莲和杜文青要去告那些在婚礼那天侮辱过钱新莲的男人们了。
杜玉梅先也在村前代销店里听见了这件事儿,回到家不久又听见她爸杜小陆不屑地跟她爷爷杜壮平说:
“哼,告?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告得了吗?他们去告,看到时衰的是谁!”
那时杜玉梅正在屋门前蹲着切冬瓜皮,听他们这样说,插进了一句道:
“只怕能告倒哩,现在不同以前了。”
“告得倒?发他的春天梦去吧!”有那么容易!那我早不用活了!”
杜小陆轻视地又说。
“只怕真的会告得倒哟。”
杜壮平带不安地开口。
那天他也和儿子一起去了闹新娘,虽然连屋也没能进(人太多,进不了),更没对新娘动手,却怕自己也会脱不了干系。
“要真告得倒,那我们怎么办呢?”
杜小陆也突然惊慌起来。
那天他不仅去了闹新娘,而且还是对钱新莲动了手的一个。要给钱新莲告倒,那他可能就得坐牢了。
“不怕,不怕。”杜壮平看看儿子,自我安慰起来,“就算给她告倒,我们大不了抓进监去给关几天,在监里还管饭吃哩,胜过在外边。”
这时对门杜文锋家的嫂子把木盘搬出门口在洗衣服。听见他们这边这样说,她接嘴道:
“就是,到时抓你们进去,倒不是衰,还很有福气哟!现在到处都闹饥荒,监里有得管饭吃,还真不错哩!”
“有福气?他这种人也会有福气?”
这时玉梅妈从堂屋里走出来,带讥讽地撇撇嘴。
“怎么没福气?有得管饭吃还没福气?”
杜文锋家的嫂子又说。
玉梅妈尖酸地:
“他要进了去,不给人打死,也会给人打残!”
“不会这么严重吧?他还会给人打死打残?”
杜文锋家的嫂子一副不相信的样儿。
“你看会不会。他那种人,要是真的给抓进监去,决不会再有什么好事情!我早就料得到他的结果!”
玉梅妈冷哼一声又说。
“我不要坐监!我不要坐监!”
杜小陆突然慌得高叫进来。
“不要这么紧张,不要这么紧张,肯定不会抓你,肯定不会抓你。”
杜文锋从他家屋里走出来安慰杜小陆说。
与此同时他在心里暗暗庆幸自己当时正要去杜文青家闹新娘时,杜仁昌喊住了他说:
“我们和文青一家人,有什么好闹的,还是一起多喝两杯酒快活快活吧。”
于是他就和杜仁昌一起在外边喝酒了。
不过他老婆从屋里也走出来时,却没他那么放心了,冲着他问:
“那时你好象也去了闹新娘,你自己不怕,我还怕哩!”
“不许乱说!不许乱说!你干啥乱说?那天我和大队长一直都在喝酒,才没去文青家哩。”
杜文锋赶快说。
“有人证明你吗?有人看见你没去吗?”
杜小陆抓住了他的“鸡脚”。
杜文锋高叫着说:
“大队长可以证明。还有钱春辉,还有他老婆,那时是他们在婚棚里招呼我们,给我们倒的酒,上的菜。”
“真的?”
他老婆盯着他。
“比缝衣针还真。”
他对天发誓似的高声说。
“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了,不用去担这份心了。”
他老婆象真的放下心来,吁了一口气说。
杜小陆羡慕起杜文锋来:
“怎么你当时就没去闹新娘,会去喝酒呢?我可最爱喝酒,却没人叫我喝。要有人叫我喝,那我也不会去闹新娘了。”
“这就叫不该闹的事儿不要乱去闹,闹了就会惹晦气上身。”
杜文锋一副神情很稳重的样儿道。
这时玉梅妈冲杜小陆道:
“你这种人就是这么没鬼用,从不知道什么事儿该闹,什么事儿不该闹。现在好了,有得你衰了!”
“你怎么这样说我啊?又不只是我一个人去闹。”
杜小陆觉得很冤屈地说。
“是有很多人去闹,但人家文锋为什么就没去闹呢?”
玉梅妈瞪着他。
“他给大队长叫了去喝酒啊。”
杜小陆又说。
“你干啥就没人叫你去喝呢?”
“我……”
杜小陆睁睁眼,哑口无言了。
这时杜克勤也跑了过来,问:
“你们在说什么事儿啊?”
“说文青、新莲告村里那些欺侮新莲的男人们的事儿啊。”
杜文锋说。
“呵,就是那日他们结婚的时候闹新娘的事儿啊?”
杜克勤瞧瞧杜文锋,又瞧瞧杜小陆。
“是呀。”
“那日你没去吗?”
杜小陆望向杜克勤问。
“没有,我没有去,我可没有去。”杜克勤回答,。
“你真的没有去?”
“是真的没有去。”
杜克勤说,同时在心里暗暗庆幸:
“好在我一向不爱出门,连新莲的婚礼也不想去,不然我可能也洗不脱干系了!”
这时只有杜小陆心里最烦恼、最不好过了,恐惧的阴影已投入到他的心灵中,弥漫在他的整个身体中,象利剑一样高悬在他的头顶上。叫他直想对天吼:
怎么那天三个人中偏偏我去了?偏偏我去了?就我洗不脱干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