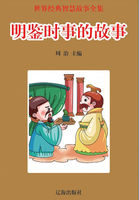杜月和有些不乐意。
“你阿姐是大人了,有很多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不懂的。”杜克林为女儿说话。
“什么?我不懂?我就不是大人了么?”杜月和叫着说,磨蹭了一会儿,咬了咬嘴唇,只得去了灶屋。
杜月雨走进卧屋去,把门关上后脱下裤子,然后拿出她今日买回来的卫生纸擦下身。血,不大鲜红的血混杂着一点儿肉末象潮涌一样从身体里涌出来。她的裤子早已染红了不少,这时拿卫生纸去吸血,那卫生纸是造得颇粗糙、不绵软的,不吸血容易烂,吸血也容易烂,不过它还是能起点儿作用,用了几张就把血吸干净了。但最后拿它包住出血的部位,它的粗糙、麻硬的感觉却叫细嫩的肌肤颇不舒服,但她也没办法,在女人墟只能买到这样的纸,这周围的女人多年来就一直是用这种劣质的纸,她不用也不行。
“两个人饮酒啊?让我饮两杯怎么样?”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杜克俭的声音,是离得较远,至少隔着两三家的。好象没人应他,他又再道:“明日我自己去买点儿酒喝。好久没买酒了呀,真叫人不舒服——小妹子(此处“妹子”意女孩、女子),你跳毽子可跳得真久啊!”
一阵硬硬的脚步声从远处响了过来,在杜月雨家门前停住:“克林哥,你家有没酒饮?要有酒饮,给我饮两杯,下奔日(过一阵子)耙田我帮你家耙。”
“没啊,我好久没买过酒了,屋家没有酒。”杜克林淡淡地摇摇头,不冷不热地回答他。
“真的么?”
“那还有假。”
他“呵呵”地从喉咙里发出了两声,静默了一会儿,随后硬硬的脚步声便又继续向巷子另一头响去。
才过一会儿,钱成山的老妈子突然在她家门口高声骂了一句:“这个炮打鬼!我放屋里头的芋头也给他偷了一个去,真是不得好死啊!”
这时杜克俭在远处“嘿嘿”地笑,没有回对她。
五
女人墟是数百年前柴头岭村的村主们和该村出外经商赚了大钱的商人们共同出资修建起来的。柴头岭村与它相距仅几百米远。在本地,柴头岭村历史上是很有一些在外地经商获得大成功的人的,这些做成了大商人的人,有一些非常热心于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让别处难以相比的地方,他们出很大笔的钱不仅在之后建了女人墟,更在之前建了统一的柴头岭村,请最好的建筑匠来设计,所以柴头岭村的村子主体是整齐、美观而又很有特色的。它采用古建筑的风格和样式,前边一个大院门,后边四个小院门:每个院门上都安有可随时往下落的重铁闸门。从柴头岭村大院正门进去有个井坪——近百平方米的一个空坪场,靠正门对去的地方有一口围边砌高到一米的大水井。井坪左边一个月门进去是杜姓的大村院,右边的一个月门进去是钱姓的大村院。这两个大村院里的房屋布局既纵横交错,又充满玄机,在几家几户连成一排而排列形成的小巷里,暗含着外人不易发现的迷宫,很多看着可以穿过去的巷子,其实是死胡同,而看着仿佛是不能穿过去的巷子,却又是活巷。柴头岭村的有些人从小到大生活在这儿,有时也会走错路,更不用说外人了。在大村院里,每段不长的小巷又挖有陷阱,平时陷阱盖有面上铺了石头、泥土的铁板机关,每家每户又有四通八达的地道。一遇危急关头,住在这大村院里的人家便马上先下地道,然后让一男人上到砌于墙角夹层的高台了望孔监视,一旦看见有敌人走过陷阱,便突然一抽铁板机关,叫敌人掉下挖得很深、插有铁剌的陷阱去,或扎死,或扎伤。它的布局之所以要这样设计,是深刻地考虑到了千百年来在中国的广阔大地上频频出现的动乱,偶尔会有盗匪闯进柴头岭村来胡作非为。自从建起了统一、严整的柴头岭村后,它们曾有过几次关起门来打狗的情况,把为数不多的闯进柴头岭村的盗匪扎死、扎伤,其中抓获扎伤的盗匪,便就地宰杀,或扭送官府。
在柴头岭村的两个小院中,数百年来一般是左边住着杜姓人,右边住着钱姓人,但这又不是绝对的,象钱成山,他因杜月雨家对门杜振财之弟杜振宝家衰败后出卖房屋,而他分家后住得挤,就买下了那间屋,从钱姓院搬到了杜姓院来。
由于柴头岭村里边住着杜姓和钱姓两大姓,这两大姓自古以来既有独立又有合作的关系,所以房屋同建在一个大院里,然后又各建了一个小院,并且各又有前后两个门通前又通后。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贫富的不断分化,现在柴头岭村大墙内那些年代久远、更加古色古香并且整齐而迷人的古建筑(有的经过重新修缮)里住的都是村里的富户或较为过得去的村民,村两边后来搭建的参差不齐的土坏房(黄泥捏制)、草木房(连土坯也不要)很多住久了都已破烂欲倒了,则是村里的穷户们住的。
天才有点儿蒙蒙亮,在沉睡中做了一个梦的杜月雨就醒来了,她一醒来就会再也睡不着觉,继续躺在床上会感受到一种折磨。因此她从床上坐起来,推开素花薄被,到灶屋里去用冷水漱了一下口,洗了一把脸,然后就先上牛棚去(农村人这时还没那么快做早饭吃)。
杜月雨家现在在村子里虽然是属于那种较为过得去的人家。而在近百年前,她家也曾是村里的穷户。当时的她家在大墙内没有房子,只在村左边建了两间泥砖房。到她曾祖父那一辈,她曾祖父挺有头脑的,不甘总居于人下,便先在家乡给人打工维持生计,后见这样下去难给自己和后辈挣下家业,就出外经商,结果赚了一点儿钱,于是回来置了两块地。到她祖父当家时,她祖父接受乃父的衣钵,继续出外经商,赚了钱不仅回来又置了几块地,还在大墙里买下了同姓一家破败户的高门大屋。到她父亲当家后,虽然出外经商的机会少了,扩大家业的雄心也没了,但田够种,衣食也无忧了。
柴头岭村的所有牛棚和一些茅寮都建在村子的背后,由一堵高高的围墙隔着。从后门出去,先见着那些用木条、木板搭建的简易茅寮,过去一点儿就见着了牛棚。
此时天色还那么早,杜振财却已挎着竹筐出来拾牛粪了,在一间茅寮旁边,他弯着腰、侧着身子用小铲将半干的牛粪一点儿一点儿地铲进竹筐里去。
“财叔公,你好早啊,别人没起你先起了!”杜月雨收住脚步,跟他打了声招呼。
“呵,是贱妹啊,你早,你早!”
杜振财张开无牙的大嘴,神情愉快地说。
杜月雨恭维他:“在我们村,每朝(早上)就数财叔公你起得最早了。”
“没办法啊,老骨头,睡不沉啊!”杜振财说。
“象你这么勤快,想不发家也不得呵!”
“哪还有那机会,我一个快入土的人,只要子孙能争气就得了,还想发财!”
“能发财,能发财。”杜月雨笑着又说,走了过去。
她家的牛棚在比较靠边上的一间,不算大,但里边圈养了两头大水牛。现在她来到自家的牛棚,打开木门就走了进去。
牛的大粪气、尿臊气,浓浓的,呛呛的,很冲人的鼻子。
杜月雨没有捂鼻子,她早习惯了,不会觉得牛粪气、尿臊气有多难闻,相反她却觉得每一点粪都是宝。
一锨,两锨,三锨……天边只露出了一点儿鱼肚白,她已在她家的牛棚起粪了。不用油灯照亮,她只凭感觉,就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粪是以稻杆、杂草为主的,因为牛栏里养着一公一母两头牛。要叫它们住得舒适些,得让它们脚下站得松软。那粪多的是牛粪,也有一些人粪、狗粪。由于稻杆、杂草多,纵横交错的,不那么好起粪,你想掀起东边一小块,它西边、北边、南边的稻杆也跟着起了,又多又沉重,很难按想法分开去,叫你颇费力气。
杜月雨今年既已十六岁,象柴头岭的其他女人一样,她的手臂就已长得很粗,至少有小碗口那么大小。但这手臂跟她的身子是协调的。在柴头岭村及周围,女人们虽然长得不苗条,但壮而不矬,不会给人难看的感觉。
在柴头岭村,勤快的、起早的人是不只杜月雨、杜振财两个的。杜月雨才在牛棚里干了一会儿,就听见外边响起了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听讲钱成山家的辉古定下了亲,是哪村哪家的?”这是杜源宗的声音。
“我不晓得。我大佬(大哥)还没跟我讲。”这是钱成相的声音。
他们说的话儿只让杜月雨听到这两句就走了过去。但他们的这两句话儿,却叫她的心“格登”了一下:钱春辉已定下了成婚的女子,而她暗恋了钱春辉好几年,从来也没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思——就算他知道她的心思,她知道自己也是无望的,他不一定会娶她为妻:在这儿,做儿女的结婚都要听凭父母的决定,自己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不是这样,她两年前也不会顺从父亲的意志,接受温财宝家的求聘了。她不能不为此感受到一种无奈的痛苦。
让一切都从此过去吧!她一个劲地按捺着自己,让自己不再去想钱春辉,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对钱春辉闭上眼睛,但她做不到。日日在她家对门出入的钱春辉的身影和他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刻印在了她的心中,此时不管怎么剔也难以剔去。
现在,在这蚊虫开始出现而不是继续销声匿迹的清晨,杜月雨身上、脚上都遮得严严实实,只有两根粗而壮的胳膊露出来。胳膊的肤色是较黑的,跟牛粪颜色有些相近,在这光线朦朦胧胧的时候,她那两根胳膊一挥一挥,如果不细看,叫人感觉好象也是牛粪在挥。
杜月雨累了,汗滴象夜明珠一样一颗颗地往下落,有的落在衣裳上,有的就直接落在粪草上。两根长得很乌黑的长辫,也湿漉漉地绞在了一起。
她只能先停手,用手掌从后边探进衣裳里边去抹一抹汗湿的脊背,休息一下,等气缓过来再接着干。
春播快开始了,得提早下春肥,不然秋收的收成会不好。
起粪是把牛粪往两个大粪箕盛,然后挑去田里。杜月雨这次把粪箕盛得实实的、高高的,足有一百五十斤重。她挑着它,送向稻田去。路不算远,是黑泥路,未铺有沙石,这一阵子有点儿雨下,使路面软湿软湿的,脚踏在上边感觉不时给粘住似的,叫人多费一点儿力气。因此这么重的担子,如果一直压在一个肩膀上,也会把人的肩膀压得很生疼。
扁担在肩上有节奏地起伏,步子不紧不慢。杜月雨从小就开始挑担子,知道怎么叫自己的肩膀不痛或少痛。她先把担杆略往右斜,几乎平着放在脖子后,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分别抓住箕绳,那两手又稍微用力往上提一下箕绳。走一段路她就换成担杆略往左斜,仍是几乎平着放在脖子上,这回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分别抓住箕绳,同样那两手也稍微用力往上提一下箕绳。再走一段路,她改为了让担杆垂直压在左肩膀上或右肩膀上……这样不断变换挑担子的位置,虽然牛粪很多很重,叫她浑身汗珠滚滚,短褂贴在身上,但她也不觉得肩膀压得有多痛了。
天边的高山和丘陵,一重连着一重,一重叠着一重,有的连向高远的天际,有的却叠向坡度颇缓、翠绿茂盛的丛林。有的线条粗犷,有的则线条柔和。灰色厚重的云层,此时还没有阳光的照临,明晦变幻着,叫山间的景物缺少应有的亮色。
“杜德威不是好惹的。”
杜月雨经过一处靠路边、有一棵垂下一串串密密榆钱的老榆树挨着的破泥砖房的门前时,听见一个声音有点儿熟、但分辨不出来的男人在里边这样跟不知哪个人说。
那听的男人反问他:“那就这样算了吗?”
后边的话儿,因为杜月雨没特意去听,走了过去,因此不知道再说了些什么。
一条小沟顺着田间小路向前蜿蜒,发出淙淙的水声。
牛粪挑到了杜月雨家稻田。那稻田还没从旁边的河里灌进水去,干干的。杜月雨就赤着脚走下田里。把两粪箕的牛粪分别捧了抛撒到上边,有些地方觉得不大均匀的,就用脚搞开一下,搞散一下,让自己看着舒服一些。